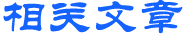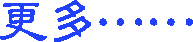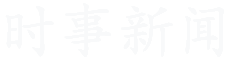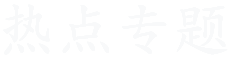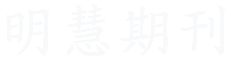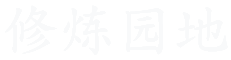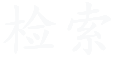我在监狱的那九年
二零零一年三月,我被绑架到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那一年我二十五岁。
在中国生活过的同修都知道,中共的强制洗脑无处不在(考政治一直考到读研究生,工作后还有所谓“政治学习”),在你刚刚懂事、还没有认识字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你能看到的漫画书,马路上的宣传画,收音机里面的广播等等。中共一方面给你灌输党文化,一方面以上大学才有出路为诱饵,让你在文山题海里面挣扎,最终能上了大学的所谓的佼佼者,却往往是中毒最深的受害者:无神论和進化论深深的刻到了这些受害者的脑子里面,我就是其中一个。这些邪恶的理论,在我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屏障,以至于在我被绑架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感觉自己与法隔着一层什么,使自己经常处在一种“希望自己明白,希望自己坚定”的痛苦的状态中。表现形式上就是,自己在和在押人员讲真相的同时,自己内心还是不断的反问着自己,为什么修炼,为什么坚信这部大法等等初级问题。在思考的过程中,每过了二十天左右的时候,头脑就会非常清晰,内心对大法就非常坚定。然后过大约一周的时间就又糊涂了,感觉就象剥洋葱皮一样,一层层的剥。这种情形周而复始,将近持续了四年的时间。
在海淀区看守所,一个号里面只有一个修炼人,没有人交流。在我進看守所大概二十多天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正念越来越弱,快要坚持不下去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当时的号长,一个没有文化的刑事犯,突然和大家说,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解解闷:说美国有个叫查德威克的职业游泳运动员,在她成功横渡英吉利海峡两年之后,她决定再次挑战自己,从加利福尼亚海岸对面很远的一个岛,游过海峡,到达加州海岸。横渡的那天早上,海边突然起了大雾。查德威克入水没多久,就看不见护送的船只了。恶劣的天气并未影响她,她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加州海岸。十五个小时后,她已冻得嘴唇发紫、感觉体能消耗到了极限。又坚持游了三十分钟,查德威克终于发出了求救信号。但上船后她才知道,自己离终点只有一海里。最后那位号长说,一定要坚持,也许你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他讲完的时候,我的眼泪差点掉了下来,疲惫不堪的心里一下子充满了正念,我知道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我。
几天后,我被转到了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就是传说中的半步桥44号,之所以叫半步桥,是因为那里是关押重刑犯的地方,很多都戴着脚镣,走路只能半步半步的走,所以叫半步桥。我的好多清华校友包括刘文宇都曾经被绑架到那里迫害。
看守所共同的特点是:寂寞、拥挤、饥饿和不被尊重,每天从早到晚的在木板上坐着。北京市看守所的环境不象海淀区看守所那么紧张,我的感受是之前来到这里的同修开创出来的,我们可以背着警察用记账的纸做成一个小本,并将师父写的诗和短的经文写在上面。一方面自己看,一方面给有缘人看。如果有新進来的同修,会背一些新出的经文,再写到上面。《秋风凉》这首诗,就是那个时候和一位北京的同修学会的。那时的我们每位同修都在讲清真相并尽力做好,赢得了在押人员的尊重。号长把整个监舍的账务本和公费放到我的手上保管,在收获信任的同时,我们也就有了纸和笔默写师父的经文。而当有的在押犯人离开的时候,他们会很真诚的说上一句“再见了,法轮”。
佛法修炼是很玄妙的,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二零零一年年底的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有两句诗打到我的脑子里:“轻舟已过万重山,两岸猿声啼不住”,之所以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这两句诗是倒着说的。当时悟到是师父的点化。后来在二零零三年初,师父《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传到监狱里面时,我才发现,师父开篇说了“大家好”之后直接就说出了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1]这两句诗。在一起被关押的同修知道了我这个经历,感叹道“妙啊!”
二零零二年六月我被转到了辽宁省辽阳铧子监狱,那里是一个水泥厂,周围的环境很差,吃的更差。每周能有两次细粮,其余的都是半生不熟的苞米面窝窝头或发糕。冬天的菜汤和在北京市看守所的一样,基本上是刷锅水加上几片叶菜。到了夏季几乎顿顿都是那种角瓜片煮着吃,以致在获得自由之后的任何时候,看到角瓜就反胃。
刚到那里,我们每个修炼人身边都有两个包夹,同修之间不能说话,彼此之间只是眼神交流。随着和包夹讲真相,包夹对我们的看管就没有刚去的时候那么严了,我们在其他在押人员不注意的时候,给对方背师父讲的法,或简短的交流。每当有新经文传進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约个时间到水房或其它地方,趁别人不注意时传到手里,或者一个人端着空的茶杯,另一个人找机会将经文扔到茶杯里面等等方式,利用这种方式得到经文。那么怎么学法呢,主要的学法方式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头得露在被子外,手里拿着经文放在被子里,因为监舍是不关灯的,微弱的光线能通过被子头那里照到被子里面的手上,眼睛向里面看,就这样学。学的时候还得提防着坐在屋里面的两个夜班包夹以及走廊里面的值班的犯人,别被他们发现了。一个同修看完了,就转给另一个同修看,一篇经文大家都看上一遍,要花好长一段时间。但是越是邪恶的环境,越需要学法加强正念。我就是那个时候背会《洪吟二》的。当时想,将来如果自由了,一定要珍惜时间和机会,不要等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懂得大法的可贵。
从二零零二年开始,铧子监狱中被非法关押的大法修炼者一直被关押在第三监区,被强迫劳动,被动的听他们放的淫秽录音带,或他们让刑事犯读不同宗教中的东西强迫我们听,被迫坐小板凳等。大概二零零三年初,有七位同修开始绝食抵制迫害,要求无罪释放,这个反迫害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一个绰号叫“大头”的邪恶之徒,做灌食粥时往里吐痰,甚至在涮拖布的脏水里涮粥盆,连普通刑事犯都看不下去直说:“太缺德了!”不知这是不是恶警唆使的,恶警监区长李成新就曾在开会时恶狠狠的叫嚣:“我叫你用鼻子吃饭,我给你们灌点尿、灌点大粪!”
二零零四年六月,蓄谋已久的新一轮迫害开始,辽阳铧子监狱展开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百日转化行动,强行逼迫法轮大法修炼者放弃信仰。将十多名大法修炼者从三监区分配到其他监区迫害,我被分配到了教育科,其余的在三监区集中转化。法轮大法修炼者连平和范学军就是在那段时间在其他监区被迫害致死的。事实上,当时辽阳铧子监狱针对大法修炼者的百日转化行动是有时间安排的,什么时间针对哪个监区的大法修炼者進行迫害,它们有一个总的规划。在决定对我下手之前,与我同龄的大法修炼者连平已经在七月份被迫害致死。
在二零零四年九月初的一个上午,教育科的几个犯人将一个装满旧桌椅的小屋子清空,当时监控我的包夹李彬和我说:你现在赶紧“签字”吧,如果不写“五书”(指放弃信仰的各种文件),你接下来的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我的内心很坦然,告诉李彬:“我不怕,我不会放弃(信仰),也不会有任何事情”。过了一个小时,奇迹出现了,那些清空小屋子的人将旧桌椅又搬了回去。针对我的迫害就这样结束了。而人间的表象是什么呢?两个小时后,监控我的另一名包夹杨毅男(原沈阳市副市长),回来告诉我,就在当天上午,监狱长赵宇山、常务副监狱长和教育科科长等专门针对我的情况又一次开会商讨,把杨毅男叫去参与讨论,最终的结论是暂缓强制转化。杨毅男说你知道吗?我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和监狱长们据理力争,说:王欣把学业、前途、家庭、爱情都放弃了,你们逼他,会有什么结果?如果真搞的玉石俱焚,对监狱有什么好处?接下来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保护你吗?有一天早上我咳嗽,上不来气。全监舍的人和我相处了那么长时间,没有一个人管我。你刚来,还是被我监视的对象,就把我扶起来,给我倒水,还扶着我在监舍里面蹓跶缓解病情。你可能没放在心上,我心里都记着呢,只是嘴上不说而已。
但是随后教育科却背着我到家里面给我的全家录像,让我的家人轮番上镜头劝我放弃信仰。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沈阳463医院里面录制患尿毒症的母亲透析的镜头,目地是道德绑架,逼我转化。更恶毒的是,他们向我母亲许诺我会“回心转意”,然后会很快减刑释放。思子心切的母亲信以为真。与此同时,教育科狱警回到监狱后将录像放给我看,并告诉我说母亲已经病重,要想见母亲一面没问题,但是必须放弃信仰。在中国监狱,对于那些真正杀人放火的罪犯,当父母病重到最后时,都可以从监狱回家看望父母;而我当时只是因为维护一个人的起码人格和宪法的基本尊严,竟不能回家看望母亲最后一面。其实以我母亲当时的身体状况和她的医疗条件(她是干部退休,有较高的医疗保险),再维持两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经监狱的哄骗,她的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于二零零五年初抱憾离世,最终也没能见自己儿子最后一面。当我父亲到监狱告诉我母亲离世的日子时,我既难过又惊讶。因为就在母亲去世那天的夜里,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在梦中,三监区的一名大法修炼者叫常万亮,指着外面的天空说:王欣,你看看那是什么。我向天空上看去,看到一个银河系,那个银河系向我传达着一种很温馨很眷顾的信息,没多久,那个银河系就像礼花一样的爆炸解体了。
从二零零三年开始一直到二零零六年底,大法修炼者们在辽阳铧子监狱的绝食抗议几乎没有断过。大到要求无罪释放,小到不剪光头。在二零零五年九月和二零零六年四月为了维护修炼人的合法权益如不戴胸卡,不调铺位等,我参与绝食了九十九天和一百四十多天。恶警在我绝食期间对我的迫害,和之前绝食的同修所遭受的迫害是类似的,在警察的纵容甚至是授意下,一些犯人干了很多缺德事。那名叫“大头”的犯人,就是警察身边的红人,是负责给我们“做灌食饭”的:他把熬苞米糊的锅放在厕所里小便池的台子上,说是怕热着我们,在那里晾凉。一年大部份时候,厕所里面会有苍蝇飞来飞去,卫生情况可想而知,而且他恶习不改,很多人看到它往锅里面弄脏东西,不只一个人到我这里骂大头太损(德)了。由于我们不配合邪恶灌食,所以我们是被值班犯人抬着或拖着到警察的办公室里面灌食的。灌完了再抬回来或拖回来,有时会直接给扔到监舍地上。
到了二零零七年初,由于大法修炼者们的不懈努力和巨大付出,我们的修炼状态发生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不配合点名,不报数,不参与奴工劳动,不坐小板凳,不配合武警搜查。同修在与家属接见时将真相小册子带入监狱,在监狱里面大家开始用真相小册子讲真相。到了二零零七年的四、五月份,同修将电子书带入监狱,一位姓刘的同修悟到师父在法中讲过“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2]于是他开始把电子书誊写到纸上,刚开始的时候,是半夜趴在上铺上写,后来白天坐在床上写,写好后就分给大家让大家抄写。大家的心性那个时候也都上来了,所有的同修一起公开抄法,还有的同修是白天晚上都在抄法,累了就睡一会。有一次搜号,一群小武警将一位同修抄的法搜走了,那位同修告诉我他要绝食抗议,我说我和你一起抗议。也就半天的功夫,警察就把他身边的包夹叫去,把他抄的法还给了他。能感受到,那个时候铧子监狱另外空间的邪恶彻底崩溃了。我们早晚六点和中午十二点集体立掌发正念,此时的警察对我们视而不见。而身边的包夹每半个月就换一批,按照警察的说法是怕身边的人都变成法轮功,而他们这么做的好处是,到二零零七年底,铧子监狱的犯人们几乎都直接或间接的了解了真相,很多人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将我们在铧子监狱受迫害的大法修炼者分开,绑架到辽宁省的其它三个监狱,我与王宝金(被迫害致死)、白鹤国(被迫害致死),刘权(被迫害致死)等十余名大法修炼者被绑架到辽宁大连南关岭监狱,我与一位姓任的同修被分配到第十六大队。
刚到南关岭监狱,任同修呼喊“法轮大法好,信仰无罪”,被直接送進严管队。由于我当时身上藏了几本大法的经文,没有和他一起发声。到了监舍将大法经文藏好后,我绝食抗议,三天后,南关岭监狱的警察命令犯人们对我强行灌食。当时分给我的包夹犯人一名叫做宋德官(杀人犯),另一名叫王东(抢劫犯)。第一次灌食时,他们一人拽着我的一只胳膊,在地上拖着,从十六大队的三楼监舍先在楼梯上拖到一楼,然后又拖到距离三百多米远的监狱医院。当时是冬天,我的腿和脚多处被磨破。当时我的内心是非常难过的,我当时的想法是好不容易在铧子监狱将环境正过来,没过多久又换了一个新的迫害环境,我想以死抗争。说来也巧,就在我所住床的上铺的夹缝里面,我发现了一个刀片。当半夜里我打算走极端时,我感觉眼前出现了一个穿黄色袈裟的人,并打出一个意念到我的脑子里给我说,“这是我教给你的吗?”“你怎么能这样做呢?”这个意念一直重复了好几遍。我悟到是师父不让我胡来,就赶紧将不好的念头放弃了。
一个月后,我因为拒绝奴工被送進严管队。
南关岭的严管队,每间牢房约四平米,高约三米,顶上有一个天窗,一進门是便池和洗手盆,睡觉时要求头冲着便池睡,极尽侮辱。最里面有四间牢房,牢房的墙壁上贴着厚厚的胶皮,防止里面的人忍受不了折磨而撞墙自杀。门两侧相对的墙上,离地面约三十厘米的地方分别有两个大钢环,这两个钢环距离一米八左右,每个钢环上面又顺序套着三个小环。我和另外二个同修就被分到其中的三个牢房。
我们被押進南关岭监狱的严管队的时候,都给带上死刑犯才用的脚镣,同时也戴上手铐,直到从里面出来为止。我被直接分配到最里面的牢房,進去后被命令面对着墙,将两腿分开,左右手分别带一个手铐,手铐的另一端分别从我带的脚镣的环里面穿过去,扣在了墙上的环上。这种姿势很痛苦,除了吃饭和方便,我被一直持续挂在墙上三天三宿才放下来。三天后,也是一只手戴着手铐的一端,手铐的另一端扣在墙上的铁环上,这样你只能在那里坐着,不能移动身体。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一只手铐到墙上面,晚上睡觉身体一动就会惊醒。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三、四个月。大约到了二零零八年的三月份,我被分配到了中间的一个牢房,進到这个牢房时也是戴着手铐和脚镣,无论吃饭、睡觉还是上厕所解手都不给摘下来,从早到晚都是在地板上坐着。到了四月末,我绝食抗议四天要求炼功,当时的狱政科长于鈞(音)答应了我的要求,将我的手铐摘下来。这样,我可以在中午和早上炼功。等我炼功的时候,严管队的犯人就不用再坐板了,严管队的警察说,他们也跟着借光了。
严管队的牢房里面有洗手盆,但是下面却没有下水管,洗手盆中间是一个大洞,底下是一个垃圾桶在接着,估计怕犯人利用下水管自杀吧。我白天坐在严管队里面,通常是自己学法或发正念,累了的时候会想一些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胡思乱想,一旦我想的不对了的时候,洗手盆里就会有一滴水滴落到垃圾桶里,发出当的一声。如果我想的问题很离谱的时候,声音就会非常大,提醒我不要再想了。但是有一次我特意看了,洗手盆里面是没有积水的;还有就是二零零九年回到监舍后,如果自己的思想跑偏的时候,监舍窗子的铁栏杆就会发出“嗡”的一声提醒我不对了。但是没有人去敲那个铁栏杆。我去问包夹,听到什么没有,他们说什么也没听见。
到了八、九月份,严管队的收拾卫生的犯人换了一个叫做李林的杀人犯,这个人非常坏,给警察出各种主意来整治我们修炼人。他找借口禁止我炼功,在伙食上克扣监狱给的粮食,经常性的羞辱、谩骂等等。在八月份以后到十一月底再次绝食抗议之前,我已在严管队绝食二次,每次绝食后第一次灌食时,十六大队警察都是找几个犯人将我从严管队中拽出来,然后在监狱的院子里面拖到五百多米远的监狱医院,以至于腿部、臀部多处擦伤。而且在这过程中,我的裤子都会被磨下来,他们就这样拖着我在监狱里面,为的就是折磨加羞辱。如果看你没有被吓退继续绝食,就用一个手推车把你在严管队和监狱医院之间接送,不再明目张胆的那样干,而是在灌食的苞米面糊糊中加上大量的盐,致使我上吐下泻。到了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我又一次绝食要求炼功。这一次对我的折磨可以说丧心病狂。在绝食期间,他们将我挂在墙上,和刚刚進严管队时的姿态是一样的,唯一区别就是晚上将我从墙上摘下来,允许我睡觉,而睡觉时除了将我的一只手腕扣在墙上之外,脚上的镣铐中间的链子也铐在了另一个铁环上面。
在灌食的时候,十六大队王姓队长和张姓队长在我极其痛苦的情况下还用电警棍电我。在监狱医院里面,我躺在灌食的床上,王姓队长拿电棍电我的脚、腿和手。电棍啪啪的响,我一声不吭,以致张姓队长把电棍拿过来向床上放电,还说,电棍坏啦? 发现电棍没坏,就继续电我的手脚。整个屋子里面静的出奇,只是听到电棍啪啪的响,犯人都吓坏了。灌食的浓盐水不允许你当时就吐出来,否则再灌。然后他们把我再弄到严管队,一進严管队的门,马上就哇哇的呕吐,然后就是解大手,将盐水排出。这样的灌食一天两次。第二天灌食时他们还拿电棍电我,当我问王姓队长为啥打人时,他居然说:谁打你了,谁打你了!由于我的坚持,七天后他们不再敢用浓盐水灌食,可此时我已经被他们迫害的持续高烧,肺里面烧出两个洞,吐黄胆水,喝什么吐什么,更不可能吃东西。也就是第七天,我迷迷糊糊中看到了七艘船,中间那艘是银子做的,其余六艘是金子做的。我心里清楚,是第四天的时候我父亲来劝我吃饭时我吃了半个苹果。这可能是我这七天下来的收获吧。到第八天开始将我留在了监狱医院病房并找人护理,我很快就处于一种昏迷的状态。监狱赶紧将我送到大连市第三医院進行抢救,当时已经大小便失禁,然而他们还是要将我的一只手用手铐铐在医院的床头,被当时的医生和护士呵斥才罢休。由于他们害怕担责任,给我父亲打电话,让他来护理我。同时又通知我的其他家人来看我最后一眼,因为他们认为我可能活不了了。当时我的姐姐、二姑家的妹妹和三叔家的弟弟都来看我,用我父亲的话说,当时我瘦的皮包骨,已经处于弥留之际。经过医院两宿一天的抢救和护理,我醒了过来。但是大约能有一周的时间,我的意识都处于一种比较混乱的状态,一直以为还在清华读书,是母亲送我到清华的校医院看病。直到临出院的时候,才渐渐的恢复了记忆。
监狱和外面的同修非常了不起,很快就将我被迫害的情况发到了网上。但是,由于当时警察封锁消息,我的同修只是打听到我喉管插破了被送往医院。回到监狱后,我回到了十六大队的监舍,他们答应我不再让我出工。而且到了二零零九年五月份,大队的犯人出工之后,监舍里面已经没有了警察,我在里面炼功,包夹犯人基本上就不怎么管了。
在十六大队,我和一些人讲真相,有的人接受能力比较好,我就会和他说的深入一些。有一次,在吃饭的大厅里,我和一个犯人讲,“人身难得,中土难生,佛法难遇”,你看对面那个大花盆里面种的树,整天在那站着,多难受啊。没想到的是,那个大花盆里的树竟然向着我们频频摇曳,就像听懂我讲的话在不断的点头。花盆的周围没有人,大厅里面也没有风,以至于那个犯人非常吃惊,说,原来真的万物有灵,你说的都是真的。
到了二零零九年四、五月份,南关岭监狱推行新的管理模式,他们叫做坚壁清野,就是白天的时候监舍区域内不留一个在押人员。只有负责打饭及清扫大厅卫生的四、五个犯人,每天上午八、九点钟出监舍,十点左右回;下午一点多出现场,三点多回监舍。我就随着这拨人進出,直到离开监狱。
最后在南关岭监狱的一年,表面上看没对我有太严重的迫害,但是王姓队长,张姓干事和赵姓队长也是找机会迫害我,小状况不断。如有一次不走安检门就又被送進严管队,我一進严管队就绝食抗议,然后两天后就被大队领回,他们可能也不再想给我灌食了。
从到南关岭监狱一直到离开,我尽力不去配合邪恶,不报数,不干奴工,不参与点名,尽我所能的去维护一名修炼者的尊严。在离开的时候,没有在放票上面签字,在出大门的时候,大门狱警要求登记签名才可以离开。我不签,送我出去的十六大队的警察要代签,大门狱警坚决不同意,对我说:你签名不代表你有罪,只是说明你从我这里走了。如果你不签,我们不能放你,这是规定。我说:既然这样,那我就回去吧(指回监狱)。值班的狱警一下子笑了,说:那你走吧。
从進辽阳铧子监狱时开始算,一共有五十五名大法修炼者,在铧子监狱里直接迫害死两名,在大连南关岭监狱被迫害死三名,有至少两名在保外就医回家后很快离世。还有不少于五人次是被送到医院抢救回来的,有的甚至是九死一生。可见这场迫害之惨烈,可见人要从过去走向未来之艰难!
我能走过来,全靠师父的一路保护和加持,不然我第一个月就崩溃了,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
English Version: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7/11/1858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