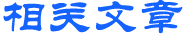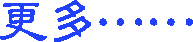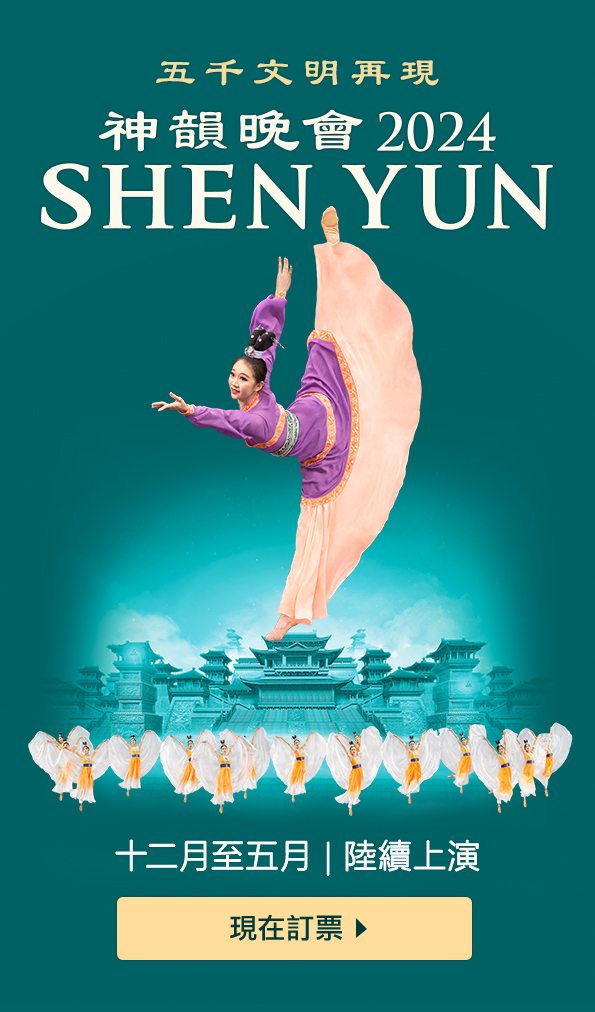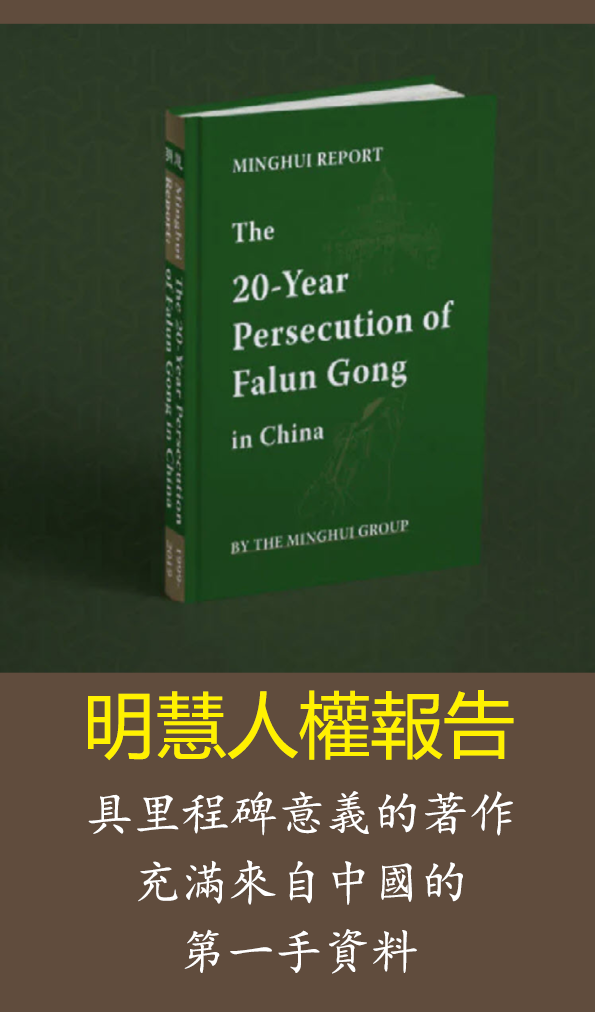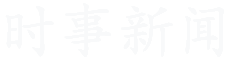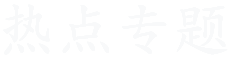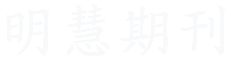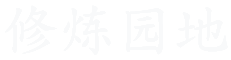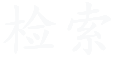一家人遭迫害 河北保定梅艳昌控告元凶江泽民
梅艳昌十五岁的女儿说:“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至现在,江泽民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中,使教人向善的大法师父蒙冤,使众多法轮功修炼者失去生命和遭到关押。我的爸爸妈妈被当作坏人非法判刑七年和三年,失去自由,使幼小的我得不到亲情呵护和教育,永远失去美好的童年。”
梅艳昌控告说:“江泽民一手发动的这场血腥迫害,给我和我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无法挽回的损失。我和我的妻子总共有十年的时间在监狱度过,是我三十岁到三十七岁,正是人生黄金年华,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在那里承受了外人无法想象的非人折磨,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和肉体伤害。也给我的家人特别是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孩子,精神上造成巨大打击,至今难以平复,甚至都不愿提起。”
“由于我夫妻被抓,幼小的孩子两岁时就被迫离开父母,由病中的爷爷奶奶带,孩子天天哭喊着要爸爸妈妈,二老也只能在痛苦中垂泪,后来,孩子嗓子哭坏了、发高烧打点滴一个多月,从此孩子变得沉默不语,胆小,精神不好。因为我们被抓,我父亲被停职(老师),最困难时没有经济来源,又被巨额罚款,孩子想吃一毛钱的冰棍都没钱买,家里买不起菜,只得到地里挖野菜,亲友怕受牵连,形同陌路,没人接济我们。”
梅艳昌一九九五年三月在北京科技大学求学期间,经一位专门研究各类气功的研究生朋友力荐,第一次拜读《转法轮》。当时全国正处在“气功”热潮中,梅艳昌认识到:这是一部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不仅限于祛病健身,更不同于一般气功,从此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作为法轮功修炼者,他时时事事用“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无论是亲人、同事、乡邻、还是路人,我都以慈善之心去对待,最大成度去掉“私”,这绝不是“与人方便于己方便”的世故,而是对一个生命的珍惜、对缘份的珍惜,是发自内心的大善大忍。
梅艳昌说:“修炼法轮大法,使我变得心胸开阔,心灵得到深度、彻底的净化,道德升华,我从人人追求的名利中一步步走出来,……能够真正为别人着想,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祥和、宽容和真诚的态度……我的身体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从小体弱多病,经常不明原因发低烧,修炼大法以后,随着心性、道德的不断提高,加上坚持炼功,我的身体不断净化,病业越来越少,现在一身轻松,大约十来年没有吃过药。每天精力充沛,一人干着三个人的工作也不累,而且任劳任怨,成为单位的技术骨干,得到领导和同事的极大信任。”
“可以说,法轮大法使我脱胎换骨,在物欲横流、私心膨胀、人情冷漠、人心、道德败坏无底线的今天,法轮大法不但给予我一个健康的体魄,祛除了病痛折磨,更教会了我如何做一个好人,一个超脱名利为别人、真心向善道德高尚的好人,这是对一个生命的根本救度。”“如果人人都学‘真善忍’,何愁百姓不安居乐业?何愁社会不稳定?何愁国家不富强?”
一、十五岁女儿梅钰珊陈述她遭受的迫害
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江泽民对教人向善的法轮功发动疯狂迫害,十六年来,使无数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使众多和我一样的小朋友失去父母亲人,成了可怜的孤儿。我的父母也在十五年前被非法抓捕判刑,受尽非人的折磨。爷爷奶奶在饱受惊恐和思念儿女的痛苦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度日如年。
十五年前的一个夜晚,警察非法抄家,使爷爷奶奶遭受惊吓,当场昏厥,父母相继被警察非法带走,刚刚两个月大的我也被带进了监狱,次日放回。从此,我便成了孤儿,爸爸被非法判刑七年,妈妈被非法判刑三年。
我的幼年和童年没有快乐,总生活在忧愁、恐惧的包围中。在爷爷奶奶的哀叹和辛劳中我一天天长大,在我印象中奶奶一直体弱多病,总去医院,因为思念我的爸爸妈妈,再加上警察常常闯到家里恐吓,奶奶病的就更重了,经常时间卧床不起。病痛的折磨,加上担忧儿子、儿媳在监狱受罪,生活的穷困,使饱经风霜的奶奶整天以泪洗面、愁眉苦脸。日历上的日期一页一页的翻,望着整本的日历,她恨不得日子一下子翻到头,能到爸爸妈妈回来的那一天。
爷爷是家中的顶梁柱,每月的工资不到一千元,既要给奶奶看病,又要照顾年幼的我,一个月下来,剩不了多少钱。那时候看着病重的奶奶、苍老的爷爷,我时常仰天自问:“为什么我们家这么贫穷?我的爸爸妈妈去了哪里?为什么别的孩子总欺负我?每当小伙伴们问我的爸爸妈妈去了哪里,我都会按照奶奶教我的回答说去外地打工了,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只是偶尔会听到同伴们说我的父母进了监狱,当时我也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都已经不记得他们长什么样子,更谈不上想念了,只是潜意识中在寻找父母。所以有时会被伙伴们嘲笑是无父无母的野孩子,也时常被伙伴们所吓:有鬼魂在你身后,它将永远附在你身后。从那时起,我便有了害怕的心理:走路要贴着墙走,还要时不时的看看后边,不敢独自一人在家,即便是一人在家,也要后背紧紧的贴着墙壁……
爸爸、妈妈带着一身伤痛相继回家了,望着他们陌生的面孔,我想:怎么日思夜想的爸爸妈妈这么老。我跟他们很生疏,我知道他们的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创伤,如果没有这场迫害,爸爸妈妈会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给我精心的呵护,给我良好的教育。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无微不至的关爱,使我感受到了家庭的欢乐与温暖,明白“爸爸、妈妈”的含义。
爸爸妈妈教我按着“真善忍”的法理对待一切。我的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烦恼多年的便秘好了,身体更加健康了,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了,能够和以前自己讨厌的人冰释前嫌了。大法教对人真诚、坦荡、不撒谎,对老师对同学要善良、尊敬和关爱,能够宽容人,不斤斤计较,我的性格也变得豁达开朗起来,更加热爱学习,远离了校园中不良习气。我的爸爸妈妈是好人,法轮功修炼者都是好人。
江泽民一手发动的这场迫害,使无数和我一样的孩子失去了美好的童年,甚至永远失去了亲人,不知道多少家庭被生生拆散,不知道多少善良的生命在黑暗的劳教所、监狱失去生命,再也见不到亲人了,江泽民撒下弥天大谎毒害了很多本来善良的生命,使他们仇恨法轮功,跟着它作恶犯罪,使教人向善的师父蒙冤。
所以,为了法轮大法师父的清白,为了更多的世人能够觉醒,为了残缺的家庭得以团圆,也为了邪恶得到惩处、正义得到伸张,我决定用法律捍卫正义,控告江泽民!
二、梅艳昌陈述他遭受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我仅仅因为回答修炼法轮功,便被北京警察当街非法抓捕遣送回原籍,关押在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大王店派出所,在暖气管上铐了一宿,期间大王店镇镇长副镇长对我进行殴打、辱骂,逼问我“发展了谁”。我觉得修大法做好人没错,政府还怕好人多吗?就如实说我妻子和妹妹也看过书。于是大王店镇政法委书记连夜带人把我妹妹梅艳芬绑架到派出所,并抄了我的家。因我妻子回娘家他们当时没得逞,第二天一早又闯到我家逼迫我父亲带着他们去抓我妻子,二十五日上午我妻子抱着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被强行带到大王店镇政府。我们同时被逼迫洗脑,看污蔑法轮功的报纸,被逼着写“保证书”等东西。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六日晚,我在散发真相传单时被人诬告,被徐水县国保警察赵保利、刘国凯(老黑)绑架到县公安局,对我进行长达四小时的刑讯逼供。我被双手反铐,踹后腿强迫跪下,棉鞋被脱掉。我因不愿牵连乡镇、村干部和家人,不报姓名,刘国凯薅住我的头发指着我说“你要是外地人,我们今晚就打死你。”赵、刘、臧某某和其他几人围住对我暴打,抓住头发打嘴巴、拳打、脚踹、电棍电,浑身都被打到了。
后来大王店镇政法书记黄福安和“综治办”一人,来到公安局,黄抡圆了胳膊一连打了我几十个耳光,一直打到没力气了;另一人自称是练什么“中华益智功”的,用力提拉铐在我手上的手铐、打耳光。后来他们又通知了县“610”和副局长闫永增,“610”戴眼镜的主任用带两个尖的电棍猛戳、抽打、电击我;闫永增命人把我架到另一间宿舍,强迫我跪下,闫用拖鞋抽打我的脸,用不锈钢老板杯砸我的头,水杯被砸出几个坑,闫说:“你的脑袋够硬的!”我向他讲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天安门自焚案不是大法弟子干的,是栽赃诬陷。闫问我出来发传单家人知不知道?我说是我自己决定的,家人不知道,闫说:“我今晚打你个半死,拉到县政府门口,倒上汽油烧了你,旁边仍本法轮功的书,明天电视台去录像报道,就说你‘痴迷’法轮功自焚,你家里人都得相信了。”当晚我的左眼球被打充血,视力下降,大片头发被薅掉,被非法“刑事拘留”关到徐水县看守所。
从十二月七日我在徐水县看守所审讯室连续遭受了十几天的刑讯逼供。参与者有国保警察李年生、刘国凯(老黑),遂成刑警中队李某某(戴眼镜的队长)、大王店派出所陈某某等等。刘国凯让我脱下鞋光脚站在水泥地上,抓住我头发用鞋底抽脸,竹条抽手,强迫我跪在椅子腿上,用另一个椅子腿砸脚踝;李年生让一人骑在我身上用膝盖压住头,一人踩住小腿,他抡起椅子腿打我脚踝骨、小腿骨、臀胯、后背及其他部位,李某某把我当沙袋练拳,让人拉着我胳膊,不错位置专打心脏部位,一连多下……我常被打的在地上翻滚,脸上、手脚流血,身上伤痕累累,腰部以下一条条的黑紫色,行走困难,特别是心脏遭到重锤,剧烈疼痛,而且无法呼吸,几乎晕过去,我的衣服都被撕坏,身上全是脚印,墙上地上血迹斑斑。国保警察刘国凯(老黑)威胁我说:“你如果不说(让我供述其他同修),我叫看守所的犯人打你,叫死刑犯打你,“熬鹰”熬死你!”
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下午,第二次开庭后,我被法警押送回看守所,同车上还有刚刚法庭上的审判员陈斌,他一路上对我不停的辱骂,进看守所后,他突然从后面狠狠打了我两个耳光,踹了一脚。
为了强迫我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不法人员对我实施了以下酷刑折磨:戴手铐脚镣、扇耳光、嘴巴、拳打脚踢;电棍电、抽打;用椅子腿、木板砸头、脚踝;重击心脏、胸口腹部;“熬鹰”;长时间撅着、坐板、罚站、几个月甚至半年坐小板凳且每天超过十七小时;关小号、强行灌食;冬天浇凉水;常年做奴工;等等等等……
在看守所遭受的体罚虐待
从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六日,我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县政法委书记找我谈话,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写不写“保证书”?我向他讲法轮功带给我身心变化,并说法轮功于国家、个人、家庭都有好处。政法委书记一瞪眼说:“你在这儿伏法吧!”看守所的指导员奸笑着对我说:“我让犯人们好好伺候伺候你!”从此我便开始了长达二十二个半月的地狱般生活。
看守所强迫我每天糊火柴盒,半夜两三点就得起来干活,一直干到晚上九点钟,中间只有两次吃饭时间,每顿饭两个馒头或酸发糕,一勺水煮菜叶,碗底一层泥沙,根本吃不饱。狱警授意犯人经常以各种理由对我拳打脚踢、罚站、撅着(开飞机)、连续六天五夜不让睡觉并不停的干活,打耳光、打嘴巴,寒冬腊月凉水浇身,强迫向家里要钱给牢头买东西贿赂狱警。
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一个我曾经帮助过的死刑犯,(一审被判死刑,我帮他写了申诉,才发回重审。)不知被谁指使突然对我拳打脚踢,用木板猛砸我脑袋,头部左侧砸开一寸多长的大口子,血流满身,一条毛巾被血浸透,缝了八针,头上留下永久伤疤。我向狱警要求控告凶手,被狱警和牢头百般推脱、威胁。
 梅艳昌被打后头上留下永久伤疤 |
由于长期遭受迫害、超强的奴工加之严重缺乏营养,我身体迅速消瘦,在家时我体重一百三十多斤,现在只有一百零几斤,被传染的浑身长满疥疮,全身皮肤起小疙瘩,红肿、溃烂、流脓,奇痒难受,晚上痒的睡不着觉,并且患上了严重的“肛瘘”(监狱医生说的),持续发高烧,会阴部分鼓起一个大包,坐不下,直到一天,鼓起的包被挤破了,大量的脓流了一裤腿,足有三四百毫升,看守所不得不把我调到“病号”监舍,并没有给予有效治疗。
二零零三年九月我和十几位同修绝食抗议迫害,看守所狱警商金彪狠狠踹我的小腿迎面骨,隔着裤子踢掉了一块皮,深夜他喝醉酒,命令犯人用硬塑料鞋底和木板拼命抽打我的脸几个人轮番打,每人二十下,直打到鼻子、嘴里到处窜血,四处飞溅。脸上的鞋印几天都下不去,头脸肿大变形。
其后,犯人牢头受看守所指使逼迫我吃东西,他叫十几个只有十七八岁的少年犯排队轮番打我的耳光,每人十下、二十下,不使劲的会挨骂,重打,用糊火柴盒的木板煽脸,直打的血流满面。后来牢头对我说,所长找他谈了要他想法叫我吃饭,可以给他记功,说所长在监控里看着呢,不打你不行。
三天后看守所把我拉到徐水县医院门诊处强行灌食,一个比较胖的、五十多岁男医生带了一大群实习的男女学生早已等在那里,学生们都带着口罩在一旁学习、观看(看样子她们已经习以为常),胖医生一边给实习生讲解,一边亲自动手并指挥别人给我插管,时不时停下来给学生讲,我被商金彪猛力按住手铐压在我腹部,手铐一下就卡进肉里,剧烈的疼痛和腹部受压使我无法呼吸,我的腿被武警按住,头也被人按住,我拼命的扭动身体不让灌,胖医生就说:“他现在不配合紧绷呼吸道,所以管子下不去,堵上他嘴,强迫他用鼻子呼吸就行了。”立刻有人拿来湿毛巾死死捂住我的嘴,由于鼻子插管,我憋得眩晕,几乎昏厥,只能痛苦的发出“呜呜”声。狱医王某某把一包什么东西倒进水里,用手搅和几下开始给我灌……。我右手被手铐卡进肉里,伤到了神经和筋腱,拇指一个多月麻木不能动。
从医院灌食回到看守所,狱警商金彪对司机说:“早知道这么简单(指灌食),我都学会了,下回再灌不用来医院啦,也不用给医院出钱了,咱们自己就办了!”果然从那天起,看守所不再拉我们去医院,就在看守所监号里以灌食的名义对我们进行迫害,第二天牢头指使十几个犯人把我强行按在地上,用牙刷把撬开嘴,捏着鼻子灌食,我的嘴被撬烂,流了很多血,牙都活动了,他叫犯人用擦便池带恶臭的抹布给我擦嘴,吩咐犯人们要把我看好,别自杀了,说阎局长、王所长都在监控里看着呢。后来得知,一个姓赵的同修被犯人灌食,往鼻孔里插管时,插到了气管里,灌食的东西全部倒进了肺部,当时就休克了。
在监狱遭受的体罚虐待
二零零三年八月,我被非法判刑七年,十月送到唐山冀东监狱五支队。副支队长邸士金、教育科长王国盛、副科长王增新、科员李恩远、谢雪刚等,指使四个犯人对我“包夹”,日夜寸步不离,不论干什么都要向他们报告。我被强迫要求放弃信仰法轮大法,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并强制我按他们的意思写所谓“悔过书”之类的东西,被我拒绝后,立即招来更残酷的迫害。他们强迫我必须每天坐高、宽不超过十厘米的小凳,从早六点到深夜三点,每天只睡两、三小时。
近一个月的时间,我被折磨得精神恍惚、头痛欲裂、恶心,腰背象折了一样,几乎撑不起自己身体的重量,我的双脚、小腿全肿了,袜子都脱不下来(消肿后,两只脚脱下大片大片的皮),狱警还以“谈话”、“下棋”、“散步”为名整夜不让我睡觉,腊月下着大雪,谢雪刚强迫我用冷水洗脸洗脚。狱警收走我自己的衣服,偷走我的生活用品,逼迫我换上囚服,还说特意批的新“囚服”,是对我的恩惠。他们还授意包夹犯人对我百般刁难、辱骂、殴打。同修郭祥宇因无法承受比我更残酷的迫害,在犯人长期毒打、罚站、辱骂“你爱哪告哪告去,撞死算了!”的迫害下,于十二月六日凌晨用头撞墙以死抗议迫害,后被开颅手术,留下终身残疾。
二零零四年一月我被转到“化工大队二中队”,狱警每天强迫我出工,生产腐蚀性、挥发性非常强的“溴素”,就是在海水晒盐剩下的高浓度卤水中加入火碱、盐酸、氯气等制取工业原料“溴”,而火碱、卤水、盐酸、氯气、“溴”都具有极强的腐蚀性或挥发性,整个厂区及厂区后面的监舍常年弥漫着刺鼻的气味。由于生产设备严重老化陈旧,生产工艺落后,“跑冒滴漏”现象非常严重,我的身体健康受到很大伤害。但是在利益的驱使下,监狱完全不顾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被编到服刑人员的“维修中队”,每天出工,维修设备、装卸化学原料、硫磺、火碱、溴素、木箱等等,以及干其它活儿。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一日在拖延了三个多月,按“疖子”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我被转到四支队监狱医院做了“肛瘘”手术。给我直接持刀手术的竟然是一个在家当过兽医的姓刘的犯人,监狱医生李德林在一旁指导辅助,还有一个姓何的狱医参与。令我非常尴尬的是,由于排泄部位术后变形,直到今天,每次便后必须用水清洗,给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二零零四年七月,冀东监狱对狱内大法弟子发起又一轮洗脑迫害,我被戴上手铐脚镣关入一个阴暗潮湿的小包裹间,不几天我就发烧、拉肚子,有好心的狱友给我泡了一杯奶粉,被狱侦科副科长王树军发现,王厉声斥责此人,叫他把奶粉倒掉了。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从开平劳教所调来的狱警郭志斌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面墙而站,他在身后突然用拳猛击我后脑,紧接着拳头雨点般打过来,又踢又踹,抓住我的衣领猛扇耳光,我被打的瞬时瘫倒在地上。后来我就此事向驻狱检察室写了控告信,被吴景友以搜身为名夺走没收。
二零零五年七月,有犯人为了“立功”减刑,向狱警告发我有大法经文,于是我被强迫每天坐小板凳,从早六点到夜里十二点,不许看书、看电视、不许和别人说话,也不许别人靠近我,由于手术后伤口又出现反复,无法久坐,我要求活动,被吴景友、杨斌用电棍电击、殴打。这种“坐板”迫害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份,使我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自小腹以下、四肢严重麻木,脚无知觉(脚上穿没穿鞋感觉不到)、针扎一样疼痛,肿胀,行走困难,中队指导员吴景友、中队长杨斌仍然不准我休息,而且为了掩盖他们的迫害,不给医治,说我装的,后来在我屡次强烈要求下和包夹犯人的反映,才带我到卫生室检查,狱医说是“末梢神经炎”,要治疗让家里买药送来,监狱没有药。因巨大的精神压力造成我整夜失眠、心悸、打冷颤、胸闷、头晕,晚上睡觉常常惊醒,出冷汗,冬天被子都湿透了。
二零零七年六月,我默写的几份大法经文被狱警搜出,我的被褥被撕烂,关入“严管队”小号,一个三点五平米的“鸽子笼”。从早到晚“坐板”,吃喝拉撒睡一切都受到严格限制,臀部、腿关节、脚、两手都被硌坏了,晚上睡觉强光灯照着,头顶二十四小时有人监视,里面闷得象蒸笼。三十三天后,他们把另一大法弟子边忠学上“死人床”,把我转到化工中队坐板,大队书记毕春利在坐镇,大队长杨善军、中队长杨斌对我大打出手。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再有二十七天我就到期回家了,又一名入狱大法弟子被关到这个中队,狱警要我保证不与他说话、接触,不影响他们的“转化”工作,我说做事要对得起天理良知,不要善恶不分,不能折腾他。中队、大队非常惊恐,向监狱汇报,狱警说支队长温英豪、政委张启星下令把我关进严管队,直到出狱那天——十二月五日。我自己带来的衣服早已被毁掉,监狱不给我衣服穿,只给找来一套保暖,寒冬腊月,刮着猛烈的西北风,我冻得瑟瑟发抖,就这样我被徐水县“610”等人接回。
两次被抽血:一次在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七日,狱内犯人抽的,一次是二零零四年十二月由总队医院联合其他地方医院采血,操作都是穿警服的正式医生,两次抽血结果都没有告诉我。
遭受的其它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在北京大街上行走时被警察盘问,因承认自己信仰法轮大法而被非法抓捕,再次关到丰台体育场,随后又被强行拉到河北省廊坊的一个中学关押,我在北京公司的一切财物全部下落不明。廊坊的官员称这里每天都从北京押来两千多法轮功学员,都是河北省的。我们在中学操场被曝晒、殴打,不许炼功、不许背书。晚上就躺在操场的水泥地上过夜,二十四日晚被保定市政府接回,连夜送到徐水县大王店派出所关押,第二天转到大王店镇政府洗脑。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六日,我在某中学发放真相传单(因前不久学校强迫学生在反法轮功条幅上签名),被抓到徐水县看守所刑事拘留。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六日,我被绑架后,一辆自行车被人推走。徐水县国保警察、县“610”人员、大王店派出所、大王店镇干部、村干部等数十人先后多次闯入我家,(后来得知,我的很多同村亲戚、邻居家都被这些人无证搜查。)不出示任何证件、手续非法搜查我的住宅,所有家具都被翻遍、撬坏,衣柜、书桌锁被砸,洗衣机、电视机都被拆开损坏,沙发垫、床垫被扔到地上、被褥衣物扔的到处都是,家里仅有的六百多元钱丢失。柴火垛、土堆、乱石堆被扒开,东厢房室内的地被挖。一台油印机、油墨、一令白纸被抄走。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七日及以后,徐水县国保警察、县“610”人员、大王店派出所、大王店镇干部、村干部等数十人先后多次闯入我家,非法搜查我的住宅,所有家具都被强行打开、撬坏,衣柜、书桌锁被砸,洗衣机、电视机都被拆开,沙发垫、床垫被扔到地上、被褥衣物扔的到处都是,家里仅有的六百多元钱丢失。柴火垛、土堆、乱石堆被扒开,地被刨开。我父母家、我的几个亲戚家很多家具都被这些人撬坏。
当教师的父亲被停止工作,家人被迫先后支付非法罚款共计一万几千元,没有出具任何票据。我父母承受不住巨大的打击,惊恐、悲愤之下瘫倒地上,从此大病不起。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七日至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五日,我在徐水县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每天被强迫糊火柴盒十五六个小时,完不成规定的数量不准睡觉,而且还要被牢头罚“开飞机”和暴打。在我被国保警察刑讯期间,双手被打的皮开血流,肿起来,回到号子里照样被强迫糊火柴盒。冬天下着小雪,就在小院子里,而且因被提审落下的火柴皮还得糊完,手上淌着血水蘸上白乳胶,伤口被蜇的钻心的疼,十个指甲被粗糙的火柴盒全部磨掉半边,露出血肉。
二零零三年七月,我被非法判刑七年,我的妻子仅仅因为帮我抄写了半张法轮功真相,就被判刑三年。同年十月十六日我被押送到河北冀东监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五日出狱回家。
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六日,我被押送到河北省冀东监狱。在五支队教育科,我被强迫每天给狱警和犯人打扫院子、监舍,然后坐小板凳;同年十二月份又转到该支队化工大队,强迫从事严重危害身体的溴素生产。
二零一一年九月,徐水县“党代会”期间,县“610”主任、安肃镇派出所到我的住处两次搜查,同样没有出示证件、手续,抄走公司配给我的笔记本电脑一台、mp4播放机一台及充电器,手机一个,后电脑、手机被要回,播放器至今未归还。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至今,每到所谓“敏感日”县“610”、国保警察、镇干部、村干部还有其他一些单位的人都要闯到我家或工作单位骚扰、威胁,十六年来不知有多少次了。
“610”、政府人员总是到我家里来威胁骚扰,不管什么时间,哪怕是深夜,我们经常在睡梦中被巨大的砸门声惊醒,他们有时甚至翻墙入院,强行闯进卧室,完全没有礼义廉耻,在孩子惊惧的哭声中,他们也要威胁恐吓一番。在农忙季节,政府人员甚至会一路打听村人找到田里,使整个村子都陷入恐慌无法安宁,给我和家人制造出巨大的压力。
我们最基本生存权和做人的尊严完全被践踏,在无尽的恐惧和各种压力下我的两位亲人不幸离世,我的岳母年仅六十岁,我八十岁的奶奶在我被绑架后就病倒,二十多天后她口中念着我的名字,想见我一面,却最终含恨而去,眼睛还是睁着的,眼角挂着泪……
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使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三、妻子张艳陈述她遭受的迫害
一九九七年底我和丈夫相识,他送给我一本《转法轮》,我一看就如获至宝。我修炼前体弱多病,胃病、颈椎病、妇科病等,修炼后几个月,折磨我多年的疾病就一扫而光。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江泽民一意孤行,对法轮功修炼者发动了史无前例的疯狂打压。我和丈夫遭受了残酷迫害。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徐水县“610”、大王店镇政府人员经常闯到我家威胁骚扰,不分什么时间,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左邻右舍都无法安宁,我们经常在睡梦中被巨大的砸门声惊醒,镇干部甚至翻墙入院,强行闯进我们的卧室,完全没有礼义廉耻,在孩子惊惧的哭声中,他们还要威胁恐吓一番。在农忙季节,政府人员一路打听村人找到田里,使乡亲都陷入恐慌,给我和家人造成巨大的压力,我们根本无法生存下去。他们还暗中派人监视我们一家人的日常活动,随时向镇政府报告。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六日夜十一点多,大王店镇政府的人去我娘家抓我,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疯狂砸开门,把我和两岁的女儿强行带走,我的老父亲苦苦哀求他们,不要把孩子吓着,有事明天再说,被他们野蛮推搡。把我们母女强行带回婆家,到家后疯狂搜查,把家里翻个遍,家具全部砸坏,衣物、使用物件扔的到处都是,公婆当即吓得瘫在地上。后半夜又把我们押到乡政府,十几个男人把我围住,高声叫骂着殴打我。这些流氓强迫让我脱掉棉鞋,光脚站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用鞋底猛抽我的脸,用棍棒打我脚面、脚踝骨、小腿骨,折磨我七天,家里托人花了很多钱才把我保回家。
当天晚上,另一帮国保警察、派出所警察、镇干部去保定抓正在上班的妹妹梅艳芬,大王店派出所的人把我和妹妹关在一个大屋子里,两头一边一个,不许说话、接触,恶警使劲扇妹妹嘴巴,满嘴污言秽语,刚刚二十出头的妹妹非常单纯、善良,没见过这样的流氓行径,气愤、委屈、恐惧,痛哭了一夜。后来她又被关押到徐水县“八四”洗脑班,在那里,她被殴打、侮辱、罚站、不许睡觉,强迫看污蔑法轮功师父的录像,一个羸弱的小姑娘被恶人们折磨的几乎精神崩溃,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留下抹不去的恐惧阴影。
从此隔三差五,镇政府的人到我家威胁骚扰更加频繁,致使我有家不能回,那时我丈夫被抓进看守所迫害,生死未卜,他们拒绝家人探视。爸爸受牵连停止了工作,又被巨额罚款,没有经济来源,一家人生活陷入绝境,为了撑起这个家,躲开不法之徒骚扰,我到外边打工,他们又找到工作单位非法搜查我的宿舍,威胁我,无理要求老板把我辞退。
二零零三年七月徐水县法院把我骗到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二零零三年十月我被押送到太行监狱。在监狱中被强迫洗脑,看污蔑师父和大法的录像,每天强迫干奴工到半夜一两点,派四个吸毒、拐卖妇女犯看管我,失去做人的尊严,我和家人丈夫的通信被任意扣押、拆看。
江泽民滥用职权和国家资源,在中国发起并维持这场对善良民众的迫害长达十六年,对法律和人权的践踏也持续了十六年之久,耗费了巨大国力、财力、摧毁了道义良知,使中华民族的道德陷入空前危机,我们最基本生存权和做人的尊严完全被践踏,在无尽的恐惧和各种压力下我的两位亲人不幸离世,我的妈妈因为整天提心吊胆,一听到街上有汽车响就以为又是来抓我们的,立刻就血压升高,一天突发脑溢血,撒手而去,年仅六十岁。我八十岁的奶奶在我们被绑架后就病倒,二十多天后含恨而逝,死不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