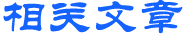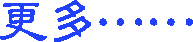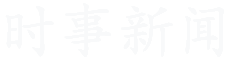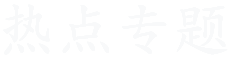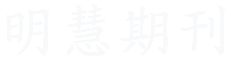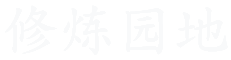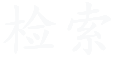在发挥最大效力救度众生中走向修炼成熟
一.大法弟子要用正念抵制迫害
在我被邪恶非法关押的初期,我还幻想着让邪恶理解我们,我要用我的“忍受”让它们明白我是好人。可是一次次的退缩,招来的是越来越严厉的迫害。我也曾表面放弃我难以割舍的大法,让它们明白大法弟子是没有危险的。虽然这么做,我的心在流血,可是迫害没有停止,它们更卑鄙的企图让我上电视批判大法,去“转化”其他大法弟子。我渐渐的醒了,看明白邪恶早就清楚我们大法弟子是什么人,但它们就是要让我的精神死亡、象行尸走肉一样活着,再進一步让我的肉体也消失、让我死也死的可耻。
我从被单位监视到戒毒所又到拘留所,再到劳教所,越退缩处境越险恶,甚至上厕所、喝水等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这样我依然“忍”,可是我周围的学员接二连三的被“转化”了。我开始抵制“转化”,向做“转化”的邪悟者做反转化工作,结果邪恶不再让我接受洗脑,精神折磨停止了。这令我受到鼓舞,承受肉体酷刑折磨要比承受精神折磨容易的多。
随着我的抵制强度增大,邪恶对我的约束渐松。我不断的争取着权利,上厕所的权利、喝水的权利、行走的权利、闭眼的权利、盘腿的权利、炼功的权利、進出门不报数的权利、不穿号衣的权利、不背监规的权利。多次绝食,多次蹲小号,多次挨打,一切都是经过付出才得来的,路走的很艰难,不管怎么样,到后来我身上的束缚越来越松了。我可以自由炼功、发正念。当我从劳教所回来时还觉的自己做的不错。
当我静心学法后,才发现与师父的要求比,差距是如此的大啊!“七·二零”时师父已经把我们都推到最高位了,我们也具足一切功能与神通。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心性跟不上,认识不到,也不相信自己会有这样的能力,更谈不上使用功能与神通了。对自己不相信,根子上说是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成度不够,没有达到金刚不动。
自己以为聪明,用人的“忍”来换取邪恶的“理解”。这却正是漏洞所在,使邪恶抓住了迫害的理由,假如我当初就做到“爱怎的怎的,我就炼了,我就是大法弟子,谁也别想改变我!”那我就不必吃那些苦了,而那些自己认为做的好的“闪光点”却都是师父在背后替我承受一切。
我这时才体会到师父说的“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哪!”(《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的涵义,我们遭受的痛苦,师父时时事事都知道。由于我没正念正行,不是用神的一面消灭邪恶,而在用人的一面硬抗,给师父带来许多麻烦。
我造成的麻烦在于“心不正”,也就是念不正,没有真正做到金刚不动,坚如磐石。如果没有“放弃修炼”的表示,以及后来许多“聪明”的行为,那么这一强加于我的迫害也就会化为乌有。其实我们现在的每分每秒都是师父用巨大承受换来的。
二.揭露邪恶 改变生活窘境
我二零零一年从劳教所获释回家,开始并没有从法理上认识如何参与正法進程,每天只是按序认真学习师父讲的所有的法,阅读《明慧周刊》,继而开始抄写《转法轮》。但是觉的提高的很慢,近一年才渐渐理清了思路,从消沉中爬起,开始与同修较多的接触,看清了自己有怕心,对克服眼前的困难没有决心。
我开始出来找工作,解决经济困难,我干过多种工作,吃过各种各样的苦,深受社会底层小人物排挤。还没从经济困难中走出来,养活自己都困难。后来有搞保险工作的人,引荐我去参加,还好由于我工作努力,加上亲朋好友帮助,我的经济困难暂时缓解了。
可是中国的保险业非常不正规,我越来越感到工作的压力难以承受。我觉的我应该从事我的医生专业工作,可是我的执业证书被原单位扣下了,多次去要,他们也不给,说“你找到了接收单位,就给你执业证书,哪个单位能接受你这个非法行医者?”可是我当时竟然被蒙住了,相信了他们的谎言,去了一个又一个招聘单位,可没有人接受我,但招聘单位又不明说。后来我去看望我的同学,我的同学分析了事情的原委,要我还得从原单位下手。
我再次回单位逐个找相关人员谈话,态度坚决,必须给我执业证书,他们再用原话搪塞我时,我说:“找哪个单位是我个人的事,无需你管。”后来直接管事的人竟撕破脸皮,开始污辱我的人格,我也不与他争辩,只告诉他要为此承担责任,随后我就去找他的上级,就是院长。
到院长办公室,院办秘书说院长不在,问我有什么事,我把事情经过叙述一遍,他说院长一时没空,我把手机号码留给院办秘书,她推说院长很忙,让我再等等。我说请转告院长,我不能再等了。
回到家,我就开始拟稿,把单位非法扣押我的医生执业证书的前后经过及相关责任人都写上了,内容限制在一张A4纸内。去复印社打字了二十张,其中一张用牛皮纸信封封好,信封上写上院长的名字收。再过一天我就又到医院去了,把这封信交给院办秘书,把打印的材料拿一份给院办秘书,告诉她,这和给院长的信中内容一样。又给党委办公室、人事科、医务科各送一张,剩下的我就站在医院大门口,发给临床各科的主任或护士长,前后不过半个小时。
又过了不到半个小时,我的手机响了,打电话的是直接扣证责任人,他说:“院长要我给你再补办一个证,原来的证丢了。”他让我不要再闹了,接着就开始指责我损害了他的名誉,我说:“我都吃不上饭了你管吗?你该干的事不干,还来埋怨我?”
又过了两个月,我补办的执业证书终于到手了。我去应聘了一家收入不错的单位,开始从事与我专业相关的工作。
三.把“讲清真相”与工作结合起来
由于我在工作中向接触到的人讲真相,工作了三个月我就被单位辞退了。
失去工作后,静下心来反思自我,发现自己有急于求成的心,一上来就讲,过渡不顺利,生吞活剥,不自觉的就讲高了,使对方很难接受。我觉的有以下收获:
顺着听者最关心的问题讲
多学法,多看明慧文章,跟上正法進程,思想中储存讲真相素材,以便应对不同口味的众生,每个人都是被救度的对像,只是有些人中毒太深了,一时不能觉醒。因此我们不能放弃任何讲真相的机会,在正法结束前一切都是可能的,即使一次不能唤醒被救者,毕竟在其思想深处震动了一次。
找到共识,扩大共识
交谈中,认真倾听谈话对像最关心的问题,摸清对方的身份、社会背景、找到共识,如跟农民谈税谈打工艰难,跟工人谈下岗。从对方最关心的地方开始找切入点,讲他同类人被迫害的事件,引起共鸣。中共是反人类的,对任何人都迫害,包括共产党党徒,因此对所有人都有可谈的话题。
我又去找新工作,找到了一个能从事我专业的工作,经过我的努力,工作比较顺利,我还是见缝插针的向同事讲真相,讲大法好。这次我试着站在第三者角度,不暴露身份,从历史故事、已发生事件入手,把现实与历史相结合,戳穿中共谎言。并用类比的方法让听者自己得出结论,如打击法轮功,就是又一文化大革命。他提问为什么打击法轮功?我就反问为什么打击“右派”?为什么打击老干部。知识份子“右派”错了吗?老干部错了吗?后来怎么又平反了?
患者接受了讲真相,但是因同事之间关系没圆容好,同样受到干扰。因为有同事向上级告密,领导多次警告我,最后我失去了工作。
从新找到工作后,我注意了圆容环境,努力创造一对一讲真相的条件,这样可以谈的比较深入一些。因为大陆长年搞阶级斗争,搞的人人自危,两个人谈话可以免除被告密的担忧。也注意了患者的接受能力及反应,效果不错。我又飘飘然,忘记了发正念,结果被干扰,我失去了工作。
思前想后,还是自己的心太急,急于把大法的美好告诉来的人。可是中国人中毒太深,又太势利眼了,不管好坏,中共说的他就认为是对的。人们就象“墙头草”一般。我得象医生治体弱又有重病的人一样,慢慢的讲由浅入深的讲,耐心的讲才行。
自己心里觉的一阵酸楚,又安慰自己不是很多人还接受我讲的了吗?要是个个都听还用我讲吗?还有什么威德?失去工作算什么,再去找就是了。
我深刻的反思,难道讲真相就得失去工作吗?这就是旧势力安排的吗?我为什么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我悟到,大法弟子是在救人,是在做证实法之事,是不允许邪恶干扰迫害的,经常失去工作、经济不稳定也是一种迫害,必须否定,我就发正念清除邪恶。
后来我以前的一位老师介绍我去一家小医院工作,我有了独立科室,讲真相的条件改善了。我也把看病与讲真相相结合,充份考虑患者的接受能力,渐渐的我的工作有了起色,我也不十分与院方计较收入多少,只要有我面向社会的平台就行,我也不与其它科争患者,来看病我就看,没人看病,我就看大法的书。
这次我接受教训,注意了由浅入深的过渡,用浅白的语言讲深刻的道理,发挥专业特长讲自焚真相,来患者我就结合医疗专业讲真相,拿出解剖图谱向患者解释“天安门自焚伪案”效果很好。
后来也陆续受到院长警告,但我注重了发正念,并且我新工作的介绍人已事先阐明了我的身份,我就向院长讲,我就是修“真、善、忍”的,我讲的每句话都是从“真、善、忍”出发的,我不能违心的讲假话。院里也就接受了现实。
四.讲真相是修炼的重要组成部份
我改進讲真相的方法,顺着对方的执着讲,按对方的接受能力循序渐進。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是对法理、正念、演讲口才、气氛感染的综合提高。工作中我多替患者着想,免费为患者提供咨询指导,抓住一切机会讲真相,能力越来越强,效果越来越好。不强调对方一定接受,按听者接受水平,讲到不同深度。
与大陆深受党文化毒害的人谈“神”是困难的,但让人相信“神”的存在,并相信善恶有报是解开人心结的关键。我在讲真相过程中,结合人体医学特点谈“神”取得了较好效果。
首先,“神”是超过“人”的能力的一种力量,如日月运行,四季更迭都是人所不能控制的,古人把这种力量称作神力,认为是“神”在控制着一切,起名“神”“佛”“道”。我们只不过是延续古人的叫法。
其次,不承认神的存在就是在骂自己,假如我们身上的一个细胞,说没有神的存在,我的存在只不过是我“偶尔”处在了这里,那么你会想,这个逆种,我们的神经中枢每时每刻调整着内环境的稳定,控制着体内的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控制着K+Na+Ca-等离子的浓度,维持着体内酸碱度在7.35~7.45这么小的范围内,才使细胞能够存活,而这狂妄的细胞却说什么没有“我”的存在,“它”只是“偶然”的处在这么适合“它”生长的环境。假想真是如此,那么把它拿离我们的身体,它的状态马上就严峻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它就会死掉了。
这小小的细胞怎么知道“我”为它做了这么多?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为“它”做的一切不是“它”自己不能做到的吗?“我”的力量不是远远的超过“它”的能力所及吗?“我”不是“它”的“神”吗?
随着不断的开拓环境,心性的提高,患者都能接受真相,甚至可以同意签字声明退党、退团、退队了。
由于我讲真相过程中注意密切观察对方的反应,能接受的我就多讲一点,有疑问的我就解释解释,不听的我就不再讲,讲、解释、不讲不是由我决定,而是由听者的接受成度决定。听者一般什么都不说,我是通过观察听者的面目表情、身体姿势(也就是体语)得知其心理状态的。
虽然我还是被人告状了多次,院长也多次来警告我,由于环境圆容的好,遇到好人说话,都一一化险为夷了。工作了一年多,院方也认可了我的为人。后来院里把一个濒临倒闭的门诊都交给我经营,经过我辛勤努力,不到一年,这个门诊部就起死回生,并为医院带来二十四万多元的经济效益,全面扭亏为盈。在好的形势下,院方有人愿意接着经营,我把门诊部还给了院方,自己又全力投身于讲真相、劝三退的大潮中。
五.抵制孩子入“少先队”
我外甥女儿住在我这里,刚一上小学时,其班主任就安排她第一批加入“少先队”。我妈妈去告诉老师,我们的孩子不入“少先队”。其班主任说晚入也得入,谁也躲不过去。放假期间我向其班主任讲真相,给她《九评》书看,老师很开通,看懂了,自己也起化名退出了“团、队”。三年后,孩子换了班主任老师,我及时去找新老师谈话,孩子新老师没有强制孩子入“少先队”,还提我外甥女当了副班长。在家里我们安排孩子参加学法,学习成绩大幅度提高。
后来学校里换了新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要求所有的孩子都得入“少先队”。我就和同修们集体发正念清除学校的邪恶,然后去学校找“少先队”辅导员谈话,借机讲真相,讲“三退”大潮,讲大法的美好,讲人生的价值。谈完话辅导员老师再也不要求孩子入“少先队”了。
六.持续不断向家人讲清真相
我父亲知道大法好,但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整苦了,差点被整死。中共迫害大法一开始,他就看出来了,是又一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对大法产生了抵触,不敢听真相,还限制我们讲真相。
对外人能很顺利的讲清真相,对家人我却一筹莫展,为此我苦恼了很长时间。
为了跟上正法進程,我买了电脑,在同修的帮助下学会了上动态网,这使我能很及时的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就把知道的最新消息告诉父亲。开始他不以为然,我也不同他争辩。随着不断的听新闻,父亲渐渐的愿意听真相了。渐渐的离不开真相了,甚至主动来问,又有什么新鲜事?我就教会他自己上网,这样就省事多了,他不断的增强了对大法的正信,主动看大法的书了。
七.正念闯出魔窟
一年前有别的区的同修讲真相过程中被恶警绑架了,同修找到我,要我帮助营救被绑架的同修。我们与被绑架同修家属交流,家属对营救比较消极,对找常人托关系比较认可。由于自己没有把营救同修当作是救度众生、讲清真相的机遇,而单纯的看重了结果,就单独去了派出所向相关人员要人,不仅没要出人来,自己也被绑架了。当时是这样的:
去年的一天,同修打来电话,说两天前有两名同修一起出去发《九评》等真相资料,并讲清真相。被两个恶人构陷,当地派出所将她们绑架了,并将她们送去了看守所。由于老年同修一路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到了看守所一测血压高压220毫米汞柱,经就近医院复查,仍是220毫米汞柱,就把她放了,另一同修被强行送進了看守所。
见面后大家在一起研究如何营救同修,最后定下来家属和我一起去派出所要人。第二天,我与同修家属去了当地派出所,值班警察告诉,负责人不在,让我们过一天再去。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到了派出所,我就去了派出所,我在接待室警察的帮助下,找到了所长的办公室。门是开着的,在正位上坐着一个警察,旁边有两个警察。我敲门后,那个正位上的警察转过脸来问:“什么事?”我说:“听说我姐姐被你们这抓起来了,好几天没回家,家里人很着急,让我来问问。”他仰起脸说:“是抓了人,你姐叫什么名?她家在哪住?”我说:“她没说叫什么名吗?那我也不能说,我回头还得面对她,她别说是我把她出卖了。”他说:“走走走,你姐叫什么名都不知道,还问什么?”我又说:“你要不就把她放了吧,她又没犯法。”他又问:“你叫什么名?”我没回答。他又问:“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同时拿起电话拨打了个号,并站起来去关我身后的门。他挡住我,门外又来了一个警察,四个人一拥而上,把我按倒在旁边的沙发上。
他们把我带到隔壁办公室,开始作笔录,我不报姓名、年龄、职业及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要你自己不亲口说出或答应人叫你的名字,他们就不能实施下一步的迫害)。办案警察问:“法轮功有什么好?”我说:“我姐姐说她炼法轮功炼好了。”他又问:“你炼不炼?炼多少年了?”我一概拒绝回答。旁边一老警察问:“四川地震法轮功捐了多少钱?”我说:“无法统计,不过奥运会中国得五十一金二十二银二十八铜。六个数排起来正好和汶川地震时间相符,就是五月十二日下午二时二十八分,六个数字,十分吻合。”那老警察说:“那是巧合。”我说“你说巧合就巧合吧,毛泽东还有个八三四一呢?”那老警长来打了我一顿嘴巴子,恶狠狠的说:“叫你骂人。”我说:“从始至终我都没骂人。你打我,那我什么都不说了。”那个办案的警察再问我什么我都不吱声,最后他把打印的一份材料递到我面前说:“看一看,签个字吧。”我不看也不签字。
过一会,他们要带我到楼下的房间去,我不走,他们就把我抬到楼下。并找两个人看着我,不让我离开。其中有一个人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我姐姐被抓起来了,我来问问,他们就把我也抓起来了。”他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我说:“你不要问个人信息、干不道德的事。”那人就到一边待着去了。
过一会,所长又来了,要我给他时间,下午一点再找我谈,我说:“不行,你得放我走,下午一点我再来。”他说:“你还能再来?”我说:“我怕什么?”他没说什么就走了。中午警察去吃饭,只剩一名警察,我想走出去,被那看的警察阻止了,又过了一会,打过我的那个老警察又来了,把背铐换成了前铐。问我想不想吃饭,是否买点香肠或面包,我都拒绝了。
我不与看守我的警察聊天,只管发正念清除邪恶,当我觉的把派出所的邪恶清理的差不多的时候,所长又来了,问我:“你带那些材料干什么?”我说:“是给你的。”他又问:“你说抓你姐抓错了?”我说:“她犯了什么法?伤害了谁?造成了什么损失?”我接着说:“我真是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宾。”我继续解释说:“过去有一家屋里放了很多草,灶火门就对着这些草。有高人看到了,告诉这家人,屋里草太多危险,灶门对着草堆易失火,赶快把草搬到屋外,再把灶门改一下方向别对着草堆,就安全了。可那家人不听,还嫌人家多事,恶语把高人赶走了。没多久那家失火了,邻居都帮助来救火,还得请这些帮助救火的邻居吃饭,这就是人的悲哀。”听完这些所长走了,过了一会又领来一个个子不高、面貌丑陋的人,那人拍了我左肩膀一下,说“法轮”。所长说:“把你刚才说的再说一遍。”我想,他这是有意让我讲给刚進来的这个人听,很可能是让这人做伪证,我什么都不讲。他们就走了。
又过了一会進来两个警察,说:“穿不穿鞋?”我说:“穿。”他们就把鞋递给我,我穿好鞋,那曾打过我的老警察说:“走吧,回家。”我说:“给我打开手铐!”他们不给打开,那就不是放我回家。我说我不走,他们就把我抬出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门口道边上停着一辆桑塔纳警车,我不上车,他们就把我放在地上。我知道要把我关起来了,就盘上腿,立掌发正念清除邪恶。三个警察就站在旁边。过一会来了一辆面包车,那三个警察就把我抬上车。我就照样发着正念,一路到了分局法制科办手续,我在外面车里发正念。那时明显感到两掌之间存在着极强烈的能量流,我发正念:全身所有细胞对应的宇宙生命赶快行动起来,清除邪恶。请师父加持,请众神帮助。发正念的强度是未有过的。
过了一会警察回来给我照了三张照片(我闭目,立掌发正念)就走了。后来他们开车奔看守所去了。我一看路就知道要去看守所,就反思自己,以往的一切就一瞬间滤了一遍。我理性的看现实,找自我,发现了自己的许多心,名利、色欲、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等等心,还有情,怎么还这么多?我觉的好象是没修过!来不及考虑那么多了,就努力将不好的心放下。有再多不足也不是邪恶迫害的借口,我就信师信法,坚定的跟师父走。心里说,师父,弟子找到不足了,我还得出去救人呢。可又一想已经到了这一步,就让师父生往外拿,不是难为师父吗?算了,一切交给师父,我就做到我能做的最大限度。一路上发正念,正念二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全身通透。
到了看守所,他们又把我抬下车,又给我照了一张单手立掌发正念的照片。他们把我抬進了看守所,我感到发正念似乎没了反应,我想一定是看守所邪恶密度大造成的。继续发正念,不配合体检,不回答问题。办案警察与体检医生窃窃私语,意思是要长期关押。体检医生说:“法轮功绝食,灌食太麻烦。”后来说去请示领导,在这期间我一直发正念,逐渐感到能量流在加强。听他们说请示了很多领导后才同意收。后来他们把我抬進了监狱,我改为双手打“大莲花”手印。监狱的人员抬着我進了电梯,到二楼他们不抬我了,抓着我的两臂在地上拖,一直把我拖進监仓。
值班狱警要求监仓管事的“照顾照顾”。他们就开始问我姓名、年龄、住址。我什么都不回答,只管双手打“大莲花”手印,监仓内的在押人员就开始打我。他们用拖鞋打我双脸,用拳捣胸,用脚踩我手指,脚趾,甚至把我脚后跟放在床沿上,再踩我的膝盖。我一声不吭的坚持着。最后牢头说:“洗澡!”就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扒光,把我抬進卫生间放在地上,然后往我身上泼凉水,前面,后面,上面,不断的泼。我一直坚持着什么也不说,也不讨饶,最后牢头说:“行了,给他擦干了,抬出来。”我又被抬到铺板上,他们给我穿上衣服,我已经冷的抖成一团了。我努力坚持,待我能坐稳的时候,我就盘腿立掌发正念,因我知道,進来时什么样以后就是什么样,第一天炼功,以后就可以天天炼功。他们也不阻止我,可是他们却往我身上套只有犯人才穿的马甲,我坚决不穿,套在我身上我就脱下,反复了几十次他们才罢休。
晚上睡觉,我睡在地上,我多次起来发正念。反复背诵《洪吟二》〈别哀〉,更增添了我战胜邪恶的信心。
第二天,一名狱警進监仓来,牢头说这是所长,我向他点头礼貌的打招呼。牢头说我一直不说话,不吃饭,所长(实为监室管理)要我到旁边屋谈话,问是什么原因。我简单的告诉他:“我姐姐被抓,我去找警察问一问,就被抓起来了。”他要我吃饭,喝水,好有力量跟办案警察干。我说:“我冤,找不到办案警察,没办法,只能不吃饭。”他又拿矿泉水,又给手纸,让我回来了。
第二天晚上,一个狱警特意来到监仓的窗口,把我叫到跟前,又拿了一瓶矿泉水,自己喝了半瓶,说:“没毒,你喝吧,给我个面子。”我说:“我冤,给你个面子只能把瓶往嘴上一对。”其实一滴水也没進肚子。
我三天里一直发正念,早晚几乎是二十四小时发正念,半夜炼一套动功和静功。我后悔自己太鲁莽,但事已至此,只好一直走下去。我没把别人救出去,自己反倒陷進来,给师父,给同修们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可又一想,我在这里发正念,就是在邪恶的中心发正念,清理邪恶,会减轻被抓同修的压力。我能冲出去了,也给同修淌条道。
我在监仓里发正念,感觉自己在狱里,东奔西跑,清理了很多邪恶,监狱很多地方都是透亮的,我奔向透亮儿的地方时发现,那里还有层层阻挡,我努力的挣开这些阻挡,使尽了力气,可还有一层象塑料的薄膜突不破,怎么冲都冲不出去,稍一缓劲,这薄弱之处却堆起了厚重的大块大块的混凝土一样的东西,立刻就暗无天日了。监狱是活的,你往哪面冲,它就往哪面挡。
我绝食的第三天,管监仓的狱警来了,他把我带到谈话室,说还是自己吃为好,不然没有上诉的机会。看守所狱警伪善的说:“要保护好身体,才能洪法,在这里绝食是要灌食的,还要连累同室的其他人员,全室人员都得接屎接尿,并且一旦灌食后,想吃都不许你吃,一定要灌,要灌到死。”他说,一旦灌食就四肢打地环固定,要我好好想想。
我在他们的威逼利诱下,竟起了怕心,怕死了,开始吃东西了。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抬不起手了,立不住掌了。没吃东西前,整小时、没日没夜发正念也不累,吃了东西后就全变了。我这个后悔呀。我明白了之后,马上又开始公开宣布绝食。心里反复背诵《洪吟》〈无存〉。
又过了一天狱警来问我为什么又绝食了,我说太冤了,他说你可以申诉,我说我就是伸冤才進来的,越伸冤越坐牢。我说趁我清醒告诉你,二零零五年十月,明慧网已发布公告,今天任何人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个人都必须承担责任,并且从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开始至今已有五千多万人声明退出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大纪元发表的《九评共产党》就是共产党的死亡判决书。发《九评》讲真相,都不犯法,因没有给任何人造成损失。
继而狱警把我拉去医务室强行灌食。灌進去的都是浓盐水,灌食后,我昏昏欲睡,口渴难耐,舌头就象锉刀一般,动一动都痛,转眼珠都费劲,我强忍着不让自己睡过去,不断发正念,清除邪恶,一发正念就好受一点。这次我也不往外出冲了,要清除盘踞看守所的所有邪恶,不让它再关任何大法弟子了。不知是过了二天还是三天,我发现整个看守所的邪恶已经败下去了,我看到它就象是一个没有眼睛的小猪崽,满身是血,栽倒在监室的地板上。
后来狱警又二次给我灌食,灌食中我坚决不配合,灌食后办案的派出所就来接我出狱。派出所的人本打算用警车接我去医院,可是看到的状况不佳就改叫120救护车了,并且全程录像。去了就近医院,我就向医护人员讲真相,讲我是为救姐姐被他们迫害成这样,后来,恶警要抽血化验,我坚决不配合,医护人员也不硬来了。
我双盘立掌发正念全面清理邪恶,直到他们把家人找来。据同修讲,从时间推算我那一次连着发了三个小时的正念。家人来了之后我叮嘱他们谁也不准签字。我们就顺利的离开了医院。前后七天就象是一瞬间。
回来后,我通过学法炼功,身体很快恢复了。经了解外面的同修为营救做了大量工作。数不清的同修近距离发正念,数不清的同修粘粘贴,发资料,还有许多同修协助我父母去派出所要人。特别是我父亲,在要人过程中表现出超过大家预料的坚定、果敢,这与他平时听大家的交流以及独立上明慧网看资料有着密切的关系。
经过反思,我体会,当前邪恶猖獗是因为我们地区讲真相的广度和深度不够。邪恶盘踞在世人的脑中,世人就被邪恶操控着向邪党输送能量。当我们向世人讲清真相,就清除了邪恶的操控,就从根本上断绝了向邪党输送能量的渠道。形势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我知道我们最缺的就是时间,回来了,我与同修把尽可能多的时间用于做大法的工作。除了必做的事以外,我们主要就是走到大街上去讲真相,劝三退。在我们周围的人都组织起学法小组,大家在一起切磋讲真相的心得体会,互相取长补短,我们小组的人大多数都独立上网。我就从大量的常规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有更多的时间来讲清真相。我们还联系讲清真相做的好的同修跨区交流经验,使更多的同修走出来投入讲清真相,劝三退大潮。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
我决定只要生活过的去,就全力投入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大潮中。我看到现在是最关键时期,亿万年的等待,就等这阶段才能救度众生。因为许多大法弟子还没认识到这一点,还没全力投入。这就需要我们先来补充当前这个环节,当大家都认识上去了,都全力投入讲真相劝三退中的时候,形势也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一切也就不那么难了,都会很容易。
我想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中,或许不等需要我去找工作的时候,又有别的事情发生。我与同修结伴,规定每天每人必须讲真相救出一人来。即使今天讲出多少个人,不能代替明天讲的,明天还得救出人来。我们就这样一路走过来,觉的路越走越宽。
八、正念正行二次闯出魔窟
前几天,我又出去讲真相,劝三退,不知不觉走到了公交车站,那里离派出所很近。在站点上,有一个中年男人等车,那人正在吸烟,我与那人打招呼,并劝他少吸烟,对身体有害。那人没吱声。我发现他的面相狰狞,右额角有一道五~六厘米的疤,象是棒子一类的钝器击打后头皮裂开以后愈合留下来的。带着不落下任何一个有缘人的想法,我劝他要记住“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不料那个人脸色骤变。一把抓住我的前襟,就往派出所拖,并高喊让人叫警察来。这一喊不要紧,来了五、六个警察把我拖進了派出所。
派出所有个警察认出了我,喊我的名字,我不答应,因为我知道办案的条件就是非得我亲口说出我自己的名字才算数,即使警察知道的再多、再清楚,我不自己说一遍(就是我不承认),就不算数,他拿你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经过再三盘问,再三诱导,再三喊我的名字,我就是不答应,不理睬,他们变换策略,问我的住址。还要我在从我身上搜出的东西的明细表上签字,我一概拒绝。拒绝回答办案人员的一切有关个人信息的提问,不说姓名,不报地址,不在任何地方签字,这是“零口供”必须的。
我就一门心思发正念,清理邪恶,不配合他们的任何要求。
他们要给我戴手铐,我坚决不配合,他们五、六个人强行给我戴上了,那我也不配合。趁他们不注意,我就往派出所外面冲,正好我父母也来派出所要人,也看见了我。尽管没冲出去,以后我父母来要人也不必报姓名,警察也抵赖不掉绑架了我这件事了。
很快,警察就准备把我送去看守所,我不配合,他们五、六个人才把我抬上车,他们还顾虑我父母缠住他们走不了,因为从他们的谈论中,我知道每绑架一名大法弟子,国安会给相关部门两万元钱,其中给举报人一千元,因此才有人丧心病狂的干这坏事。我们抵制邪恶,不配合警察也是在救度他们,不让他们把坏事做成。
到了看守所,我不下车,他们抬着我進了看守所,我不配合体检,他们又把我抬進了监室。在监室床板上休息了一会,我缓过劲来,就双盘打坐,发正念。监室里的牢头知道大法好,没有难为我。我还是不说话,监室头问我:“本地的?”我笑笑,算回答,他也不再往下问。我继续闭目双盘发正念,一直到晚上睡觉。监室里人太多,都得侧身立着睡。我睡一会睡不着,就坐起来在脚下处发正念。炼完功接着就下床板炼动功,炼完功又上床板坐着发正念直到天明。
第二天早晨开饭时我向牢头声明绝食不吃饭。然后就发正念,不穿号服,不背监规,不报数,没事就连续发正念。上午,估计在十点钟左右,管监室的警察来了,他说你怎么又来了?我看看他没说什么,心里说:我愿意来呀?他让我出去接受提审,我说:“让办案的人回去,我没什么可说的。”他找来板车,让监室内的在押人员把我抬上,推到提审室。
我在车上打着坐。办案警察说现在向你宣读在押决定,念完后,说:“你有什么意见?”我本来不想回答,他又说:“同意?愿怎么办怎么办?”我说:“我抗议!对我的关押是非法的,我要求无条件释放!”办案人员说:“你说无条件释放得说出个理由来,说说理由吧。”我一看他们在做记录、在凑材料,就不再出声,因为我的要求已经表达完了。他们又问:“你炼功受什么益了?”这是诱供,不管你怎么说,他们只要把材料凑上就完,审批的政法科根本不看内容,只要有你的签字材料那就送劳教。他们又问姓名、住址、工作单位等,我一概不予以回答,最后,他们把写的材料递上给我,说看看吧,签个字。我接过来,一把就给它撕了,旁边的狱警急忙抢回了已被撕裂了的材料。办案警察脱口说“这得放了”,回过味来又说:“我看得砸你三年教养。”我立即心里说,你说了不算,我说了算,一天也不行,立即释放。
狱警把我推出提审室,我心里说:师父,弟子做的不好,才身陷囹圄,让您操心了。我请您管,我要把自己彻底的交给师父管,我无愧于“大法弟子”的称号。
我知道提审过程是正邪交战的关键,不容许一点闪失,对师父讲的:“当有邪恶之徒问到你们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时,可以不答理他、或采取其它回避方法、不要主动被邪恶带走。”(《精進要旨二》〈理性〉)的理有了深刻的认识。我打坐立掌,回到监室门口,在押人员又把我抬進监室,同时说:“这是在请佛呀。”
第二天,狱医指挥在押人员给我灌水,二次强行灌都没灌進去一滴水。我发正念要整个看守所土崩瓦解,我发正念在另外空间消灭它。下午监室扩音器喊我的名字,说要释放,我依然不为所动,仍然不答应。在押人员拉着我说:“喊你了,回家了。”监室门开着,许多狱警在门外看着我,我慢慢走出去,走出了监区。门外办案警察接我出了监区,出了监狱。狱门口我见到了父母,他们接我回到家。
回来后知道,与我配合的同修见我被绑架了,就立即通知我父母去派出所要人,此后我父母也就天天坚持去派出所要人。又通知尽可能多的同修集体发正念解体邪恶。在最短的时间里就一切都到位了,邪恶还没聚集就被解体了,从而大大的减轻了我的压力,使我能尽快的冲出来。同修还准备了“诉冤马甲”(白布做的马甲,上面写着派出所非法抓人的事实),要我父母穿上到派出所揭露邪恶。我们整体心性提高的很快,没等穿,邪恶就解体了。
过后学了师父《曼哈顿讲法》,我发现师父就是对着我的痛处讲的。师父指出的两个执着,正是我一直存在的、一直舍不得改的毛病。最大的不足是,我对同修的情。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与一名女同修走到一起了。她也是被邪恶迫害离了婚的同修,我们对大法都有坚定的信心,各方面配合的也很好。她经济危机,我觉的大法弟子应该互相帮助,共同抵御迫害。我就在经济上支持她。男女相处,久则生情。虽然同修经常提醒我注意小节,我认为没有发生越轨事实,就是对人家有些不尊重,这里抓一下,那里拍一下,自己认为是小事。这不庄重、不严肃,其实也有漏了,魔就趁机要整个挤進来。旧势力就借机来迫害我。其次,是脾气不好,爱把尖,心胸狭小,谁都不如自己。不能宽容别人,狱警孩子也大声小气的,气的不行。这指出的正是我的不足。我一次又一次的摔跟头,就是因为有执着,现在必须改了,时间已经不多了,发现修了这么多年,自己怎么还这么坏?这色心和不让人说的毛病还能带上天吗?留着这人心就不能修成啊!
再回头学习《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师父早在三年前就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我却没有在意,迟迟不改,屡犯不止。我两次掉進监狱,是师父慈悲,看我还有改好的决心,原谅了我,才又把我捞了出来。在同修们集体高密度发正念的营救下我才又回到了正法進程中。但这其中对救度众生起到了干扰,耽误了宝贵的时间。其实我们完全有能力制止邪恶的。我不能在理上认识清楚,才摔跟头。回头看修了好多年还这样,真是惭愧,我要好好修去一切执着。我是大法弟子,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我要做的纯正,给后人留下一条修炼的路。
被抓進看守所是耻辱,没什么可炫耀的,我写出来的意思是要大家借鉴,坚决不配合邪恶,正念足,师父就可以管的,就可以减少损失,少受迫害。
修炼是严肃的,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修炼中引以为戒,不可忽略任何一件小事,去掉所有的执着,特别要注意男女之间的不检点、不庄重,不给邪恶一点缝隙。因为你有一小点缝隙,邪恶就要扩大它,把你拉下去。我身边就有许多真正做的好的同修,心性高,功能强,能力大,在高效的救度着众生,却一点问题没出。
我现在虽然在全力做证实法的事,有时间就讲真相,可我一直没能高效讲真相,这与我个人修的有漏有直接关系,因为不纯正,所以影响了众生得救。我们每个人都代表着各自宇宙大穹巨大的体系。我们中谁修成了,我们中谁主宰的体系就被留下来了。现在说我们怎么好,都不可大意,都为时尚早,差一步也不行,必须到圆满成功才行。现在满天的众神都在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他们在严格的审查着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不是不慈悲,是“为未来的宇宙大穹负责”,这也成为正法的阻力。我们只有做正才能冲破他们的约束,就是邪恶迫害不着我们了。
此次营救过程中,同修们配合默契,我父母也在其中表现的正念十足,因此我建议大家都努力向家属讲真相,向家人讲真相需要长期的、细致的讲。我们在家人面前也不能放松自己,也要表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