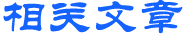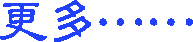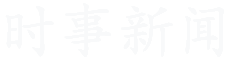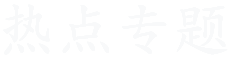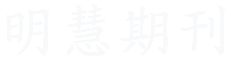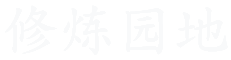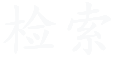只要是证实法的事 我都义无反顾
回顾走过的历程,感慨万分,每一次提高都是师父的点化与导引,每一个收获都是师父的启迪与恩赐,每一次化险为夷都是师父的加持与呵护,每一次净化与升华都是师父的承受与慈悲。弟子在此叩谢师父的救度之恩!
得度
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姊妹兄弟八个,我排行第二。因为家穷,我十岁才上学,又逢生活困难时期,光想着填饱肚子,哪有心思念书?小学毕业后回家只知道干活,从来不看书,提笔忘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一写字手就发抖,念了几年书也都就着饭“吃”了。
婚后,有了一双儿女。恢复高考后丈夫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机关工作,我也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居民,在我找到了工作后,日子才一天天好起来。
正当我对生活满怀希望的时候,一九九六年,正在上大学的儿子突患重病住進了医院。我七十多个日日夜夜胆战心惊的伺候着他,吃不好,睡不宁,最终也没有救了他的命,白发人送了黑发人。我痛苦万分,整日里哭哭啼啼,头昏脑胀,魂不守舍。精神上的痛苦导致我的身体也垮了下来:尿道炎、膀胱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各种疾病缠身,走路腿脚发颤,浑身冒汗。班也上不好,活也干不了,连累丈夫、女儿工作都不踏实,丈夫也整日愁眉苦脸,女儿郁郁寡欢,家里没了笑声。
就在此时,单位的同事向我介绍法轮功,并约我与她一起去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我没有文化,师父讲的有些内容听不懂,不过我还是被吸引住了,而且听着师父讲就觉得心里敞亮、舒服,这可能就是缘份吧!
就这样我走入了大法修炼。每天和同修一起学法、炼功,慢慢的许多苦恼、伤心也都渐渐放下了,心情好了。
时间不长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各种疾病不知不觉中都消失了。丈夫看到了我的变化由衷的高兴,只要与我修炼有关的事,无论是花钱还是出力,他和女儿都很支持我,同修来家热情接待,遇到问题还帮我出主意想办法。
他经常与他的同事和朋友讲:“是法轮功把她救了,要不我这家就完了。”同事、朋友也都很认可法轮功。
炼功的人越来越多,大法书和师父讲法录音、录像极缺,供不应求。听说书店来书了,我就赶紧去买,我想起师父的法:“给别人什么东西都不如给人法好。给他再好的东西,给他钱再多,他也是一世一时的幸福。而你给他法将是生命永远的幸福,能有什么比法更好呢!”[1]
我姐妹多,也想让她们得法。我花了一千多元钱买来了师父讲法录音带、录像带和大法书籍送给她们;还买了爱普复印机给大家复印师父的新经文和大法资料。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恶对大法的迫害开始后,形势恶劣,有的学员放弃了修炼,有的转入“地下”。我这个人有点“憨”,干什么都实实在在,不知道取巧耍滑,也没有那些弯弯肠子,大家看我实在,都愿意和我交往,再说我家庭环境好,丈夫、女儿都支持我修炼,大家信任我全家人,有事都愿意来和我们商量。
环境恶化,辅导员手里还有一部份大法书籍和师父的新讲法、经文没有来得及发下去,放在自己家里又不安全,就拿来我家让我保存;二零零零年六月,一部份同修要進京上访,有的也把大法书交我保管,我一点顾虑和怕心都没有,只要是大法和修炼的事,我都义无反顾的去做。
卸下了一大批半成品《九评共产党》
《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后,市里的同修联系了某印刷厂印刷了大量的《九评》,逐级分发到各区、县,直到各辅导站。一天晚上同修开着小面包车来到我家,说车上拉的是印刷厂刚印刷的半成品的《九评》,跑了两个学员家,没人敢留……,我一听就明白了,什么也没想就说了句:“卸车!”我看到同修眼里噙着泪花。
我把大衣柜里的被子全拿出来,把一捆捆的《九评》放好,再把被子盖上。同修还拿来了大切纸刀,告诉我放在家里时间长了也不行,要想办法尽快装订、发出去。我为此专门买了个大双肩背包,还买了厚纸书皮。晚上我背着装有部份《九评》的背包,佯装有事外出,辗转到另同修家,和同修们一块装订。这原来就是做书啊,我们连见都没见过。就比着同修以前做的照着做,那书皮还好粘,可那大切刀就不知道怎么用,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试,边做边琢磨,原来用它也有一个巧劲。只要用心去做,师父就会给我们智慧,很快就掌握了技巧,越做越熟,得心应手,做的还很整齐。做完后同修们就分头去发送,做完了也就全发完了。
有时我也往楼洞里的住家发(其它资料也是一样)。为了安全,出门时将头发盘起来,有时也戴帽子,穿上比较宽松的外套,揣上资料,就象串门一样到居民楼洞发,出来时将头发撒成披肩式,再将外套翻过来穿,与来时完全是两个人。
小型法会在我家召开
二零零五年的一天,同修约我去开法会,我正给女儿看孩子,脱不开身。同修说:“那就来你家开吧。”于是约定下午一点在我家开。因为环境险恶,法会规模都比较小,一般也就是二、三十个人。我们那个法会预计也就是二十来个人吧。
没想到别的地方的同修听说这里开法会,也开着车来了四、五个人,还带来了两个小纸箱,里面装着《九评》录音带和一些大法资料。会上他们也讲了他们的情况,做了交流。
法会结束后,我把饭焖上,同修们三个一帮,两个一伙往外走,有的取资料,有的要录音带,走的就比较晚。
最后两个同修前脚走,丈夫后脚就下班回来了。我刚把饭菜端上桌,就听到敲门声,我以为是最后那两个同修有事返回,也没问是谁就开了门。一看是两个警察,我问:“有啥事?”一个说:“听说这儿有人。”我问:“啥人?”一看就我们老俩口和一个在地上爬的小孩,他俩也愣了,有点疑惑,也有些尴尬。他们想進房间看看,我质问他:“你们这是啥意思!是啥意思!你要干啥?”在我的追逼下,他俩慌张的说:“没事,没事。”转身就走了。
后来得知,是因为来参加法会的人多,大家又是陆陆续续的向楼下走,动静比较大,引起楼下某人的注意,打电话报警了。
丈夫了解了情况后教我:“和你的同修约好,以后来时敲三下门才开,以防坏人。”
跌倒
二零零零年八月的一天午后,我象往常一样带上不干胶小粘贴,为遮人耳目,领着六、七岁的小外甥女(妹妹的女儿)去小广场、超市、商店转悠,有机会就贴小粘贴。下午三点左右,我俩从某商店出来。外面正着下大雨,我见不远处有小篷车,想坐小篷车回家,就招手让他过来。就在这时突然觉得好象有人推了我一下,我不由自主的向后倒了下去,后脑勺“嘭”的磕在水泥地面上,顿时失去了知觉。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刚苏醒过来的那一瞬间,觉得别人的声音很小、很远,知道自己跌倒了,也意识到自己是炼功人,不会有事的,便慢慢爬了起来。小篷车就在身边,我领着孩子上车回家了。
回到家告诉我妈说我跌倒了,让她做饭。说话时觉得很费劲,有点恶心,想呕吐,就到卧室坐在床上炼静功,觉得脑袋忽忽向外冒东西。炼了四十多分钟,丈夫和女儿回来了,听说我跌倒了,就让我去医院检查,我说:“不用去医院,我有师父管,啥事都没有。”丈夫、女儿也明白大法真相,也不勉强我。
这时我的小外甥女却喊着:“我再也不跟二姨了!我再也不跟二姨了!”过去她大多时间都是跟着我,住在我这儿,可这天晚上非要打电话叫她爸爸开车来接她。我跌倒时,她就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可能是把她吓着了,足见当时我摔的有多严重,对她有多大刺激。
头两三天不能翻身,不敢咳嗽。就象脑浆与脑壳脱离了一样,觉得脑浆在头里晃来晃去。奇怪的是我磕的是后脑勺,后脑勺却不疼,两边疼,疼的不能摸。我知道这是师父保护了我,让我消了一个大业,还了一笔大债。我思维清醒,坚持学法、炼功,一周后症状逐渐消失。
过了几天,我和丈夫又去那商店,走到店门口,我就给他讲我当时摔跤的过程,这时旁边一个卖东西的人说:“哎哟!那天跌倒的就是你啊!可吓人了,那么大的动静。你没事吧?”我说:“没事,我是炼法轮功的,不会有事的。”
那人还是疑惑:“你真的没事啊?”我说:“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啥事也没有。”那人感慨的说:“真是神了!磕的那么重却啥事也没有。”
去北京
二零零零年因女儿结婚,使我错失了去北京证实法的机会,觉得很遗憾。二零零四年九月底,同修约我一起去北京证实法,我答应了。我们四个人准备了许多不干胶、真相条幅和“踩江”纸片。我们四人俩人一组上了火车,我和另一同修坐在一起,她坐里面靠窗,我坐外边挨人行道。车在行進,同修悄悄的给对面乘客讲着真相;我抬头向前看,在我前排斜对过坐着一男一女,那女的行为怪异,极不正常,一会儿和那男的叽叽喳喳,一会儿盘腿做出象练功的动作。我一看就是假的,我怀疑他们是便衣或特务,故意引诱大法弟子,也没有人和他们搭腔。
夜里一点,我们正在迷糊,列车上的乘警突然来到我们面前,检查并拿走了我们的身份证,其他人却不查。我抬头一看那一男一女走了,验证了我的判断:是那俩人搞的鬼。这时我脑中闪出师父的话“正念正行”[2],我们在心中默默的发出强大的正念否定它:解体操控他们的那些背后的黑手烂鬼和恶党邪灵,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并念口诀。回来后他们又检查了我们的包,里面除了吃的什么也没有,他们悻悻的走了。旁边的人说:他们是来查法轮功的。
到了北京天安门,正赶上升血旗,我们站在人群中发正念。有许多外国游客,我们就在他们中,一边走一边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也不知道他们听懂了没有?
在天安门上没有机会挂条幅,我们就去了八达岭长城,游客也很多。我们就把真相条幅或贴或挂在城墙上,将打印的“踩江泽民”的小纸片撒在长城上,让千人踩万人踏。
我家也是个资料点了
二零零六年丈夫退休了,女儿让我们到她那儿去。我不是不想去,只是觉得到那儿人生地不熟,不利于我做三件事。我现在虽然不会做资料,但当地同修多,又熟悉,资料从不缺。到女儿那儿资料怎么办?我问女儿:“去你那儿,你能给我联系上大法弟子吗?”女儿说:“我咋联系?我还能上大街上喊‘谁是大法弟子’吗?”
是啊,联系不上大法弟子怎么办?我不能总靠着别人给我提供资料啊,人家是大法弟子,我也是大法弟子,做事怎么老依靠别人呢?这不是依赖心吗?不是有许多没有文化的老年大法弟子也建了家庭资料点吗?人家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再说师父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我等、靠、要也不符合法的要求,也是没听师父的话。想到这儿,我就和女儿商量:“你能帮我买电脑和打印机吗?能教我学电脑吗?”女儿回答说:“买电脑和打印机没问题,教你学电脑也可以,但能不能学会那得看你自己。”
女儿就从开机、关机开始教,又教我怎样打开文件,教我双击。开始手指就是不听使唤,鼠标还老动,急得我出汗都打不开。我当然不服气,越难我越要学。我文化低,全靠脑子记,学一步反复练习,慢慢的掌握了一些窍门,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看到自己打印出来的资料居然也那么漂亮,心里很高兴,我再也不缺救人的资料了。
开头打印还很顺利,后来就出问题了,有时漏墨,弄得纸很脏;有时半途纸卡住了,拿不出来;有时连供软管有空气……,找同修帮忙,他们一边修理,一边讲原理,告诉我应该注意的事情。也和我在法理上磋商,修机器先修心,要和机器多沟通;也要发正念排除干扰。他们修理时,我也仔细看着、琢磨,也会模仿实践,慢慢的也掌握了一些规律和技巧,学到了不少知识,能自己做的就尽量自己做,少给别人找麻烦。
下载、打印这很简单,因为明慧网都给准备好了。但上网“三退”就需要自己动手打字,同修教会了我怎样上网做“三退”,可我不会打字,我认识的字本来就少,又不会汉语拼音,连字的笔画顺序都搞不清楚,怎么办?同修鼓励我安装“神笔”软件,于是我买了“文采飞扬”智能版,可以手写输入字,不但解决了自己给世人上网“三退”的问题,也能帮助同修上网“三退”了。最近又在学习简单的文字编辑。
有句话叫“笨鸟先飞”。我文化低,脑子反映也慢,但我是大法弟子,我有伟大的师父,师父给我智慧,给我正念,师父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只要坚定的信师信法,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就一定能走出自己的历史,走正自己的路。
师父给了我们宇宙中最大的荣耀和让我们完成下世救人的艰巨而伟大的任务,蘸尽东海之水也写不完师父的佛恩浩荡,耗尽毕生也无法报答师父的救度洪恩,唯有坚修大法,修炼如初,精進再精進,才不辜负师父的期盼和希望。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