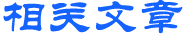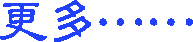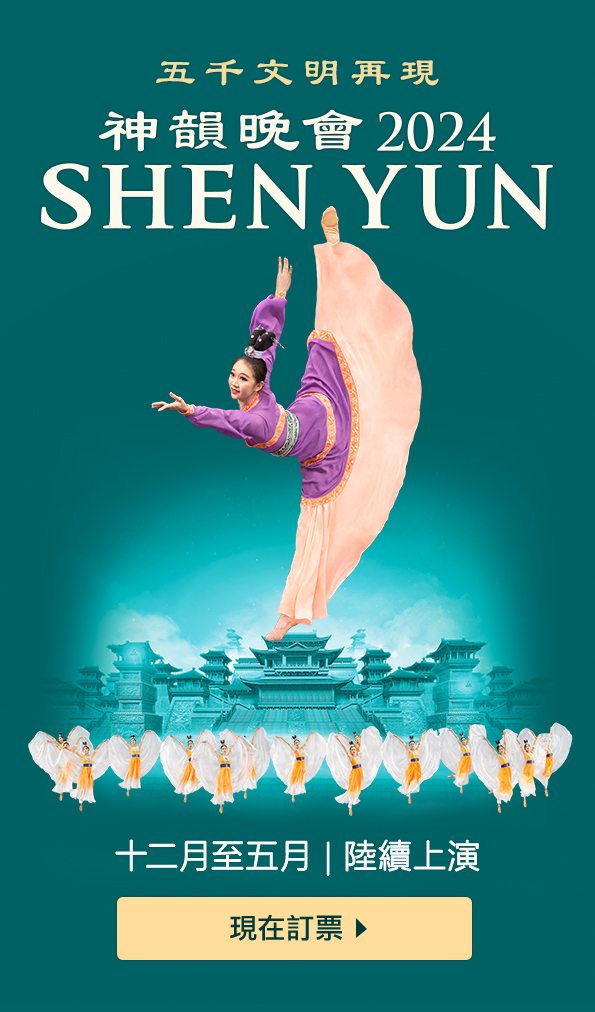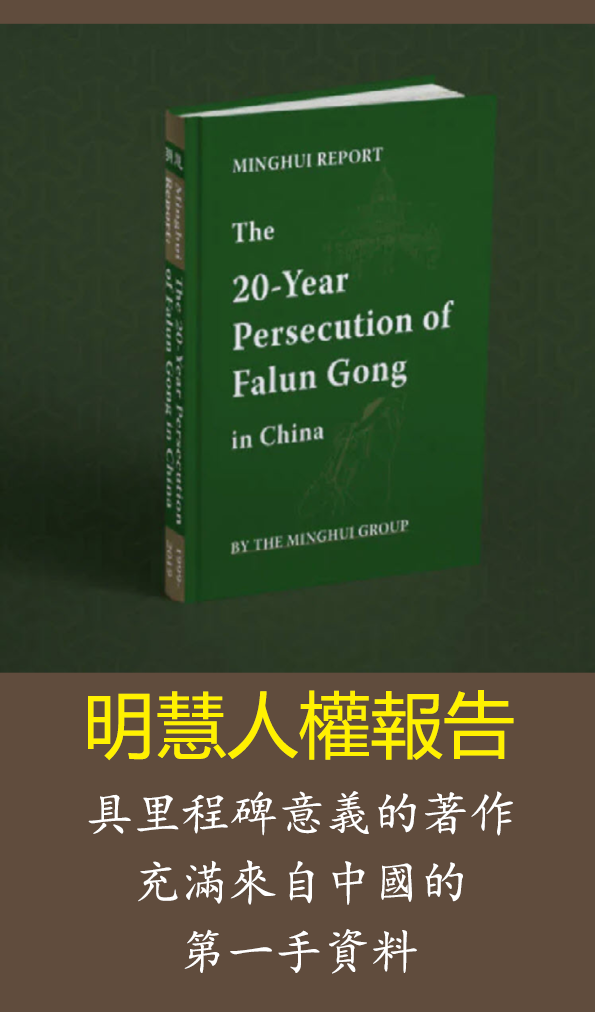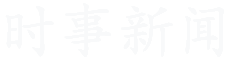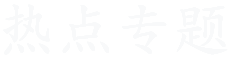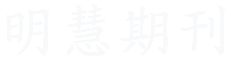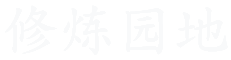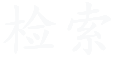广州市医生冯金桥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七十六岁的冯金桥曾任西安东郊第二职工医院儿科医生,她的丈夫和女儿都是医生。她曾身患疑难病症,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功后疾病痊愈,身心健康、愉悦。可是一九九九年之后她屡遭关押迫害。以下是她在诉状中的叙述:
一、如下所述,我是通过以下方式接触并开始修炼法轮功的:
我是西安东郊第二职工医院儿科医生,先生是广州第一军医大学附属珠江医院副主任医师,女儿也从医,我身上发生了堪称人类医学史上罕见的奇事:八四年新年,我值班,因连续抢救病人过度劳累,患了个最常见的感冒,因我平时身体好,多年全勤,小病并不影响上班和家务,根本没放在心上。可是一拖一月多,总是发冷,全身说不清的不舒服,就找一位中医名家调理,万万不曾想到事与愿违,几副药下肚,人就象掉在冰窟,怕风、怕冷。从头到脚冷气从百会、囟门、大椎、涌泉、合谷等关键大穴往内吸,而且越来越重。脚冷的穿不了鞋,手冷的不敢摸东西,腰部四周必须用厚棉被扎裹,无名的心惊胆战,坐卧不宁。仰卧时胸部好象有块大石头,压的出不来气,胃内象有块石头往下坠,吃东西就象吃了石头,又顶又坠。全身关节疼痛,冷气象芒刺一样刺入,全身没有一个地方不难受,许多症状又无法形容(我对自己都无法书写一份病历)。可是体力、精神很好,思维如常。除了胸部皮肤许多蜘蛛痣外,五脏六腑无实质病变,其它化验,Χ光等各种检查都无异常。西医大夫最看重的是病变、体征及各种检查所见等,我却找不到任何病变。自己痛苦的无法形容,可别人根本无法理解(足见实证医学的局限性)。一旦感冒上述各种症状就会持续加重且迁延不癒,那时的我,真是到了西医治不了,中医没人会治的地步。我也失去了上班和干家务的能力。随着病情的延长,也失去了职务、工资晋升的机会……
我心中十分清楚这是个世界级的难题,但我又是一个不服输要强的人,我把希望寄托于自身努力奋斗:疗养、各种理疗、各种锻炼、跑步、体操、打拳、练剑。无招了又去练气功,心内隐隐约约有一念,找个好气功能好。但气功是什么并不知道,认为练气能通经络,经络通了就愈复了。当时接触了几个气功界的“名人”,对这些人的德行很有想法,挑选了再挑选,也练了几种,练来练去稍有疗效,但又反复发作,而且越来越重。极度困难时,我都想“张榜求医”。
第一军医大学气协负责人给我介绍了个“气功师”,由于不懂,接受了他的“气功治病”,不仅骗去了很多钱,结果弄的更重:大热天坐卧于热水袋上,穿棉鞋、戴棉帽、头不能转动、眼不能视物、门窗紧闭,还得拉上窗帘、连上卫生间的本事都没有了……此时的我自嘲“只会吃饭”。
因祸得福、绝处逢生
第一军医大学,有几派气功都有人练,大家都在寻找健康,气协负责人又推荐给我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后来我得了一本《转法轮》。
那时的我整天惶惶不可终日,坐卧不宁,整天害怕,睡觉也会吓醒,头发全白,头屑如糠,头不能低,不能转动,眼不能视物,更不能俯视,还不能戴眼镜,根本没有看书的能力。用手随便翻翻书还莫名其妙的害怕,觉得能静静的死是最大的幸福……所以,书在家放了很久也没看。
一九九七年三月,有一天,不知道怎么,突然我自己戴上眼镜看起书来,一看竟然看了四十多分钟。至今,我都想不起来当时根本不能下地的我,怎么去拿书、看书……这一看,这本书把我吸引住了,使我耳目一新,谈到气功界的不良现象说到我心坎上……说到真善忍的法理让我折服……这本书仅仅看了三分之一,就深深的震撼了我的心灵,隐隐之中似乎就是“我一直要找的好气功”。我兴奋的跑去客厅,连说:就炼法轮功!就炼法轮功!已记不清我多久不能出卧室,更不知道,不记得当时是怎么跑出去的。
第二天早上醒来,感到全身铺天盖地的大大小小数不清的轮子从骨头中把冷气往出排,全身暖融融的,那种舒服美好无以言表。十数年的病痛,我已忘记了什么是舒服,只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无法形容的“难受”,和心灵上无限的伤痕、伤痛。我只知道早上五——七时是我最难过的时候,不知道身体热还是冷,盖厚还是盖薄?两条腿不知道该怎么放……此时的我惊呆了,好象都没有思维了,就那么闭目静卧……三天才回过神来。
我本身是一个顽固的无神论者,虽然也练过气功,那是体操加上呼吸引导“得气”而已,根本不知道与修炼、与佛、道、神有什么关系。但这本书看完了我好象整个人变了,脱胎换骨了!世界观变了!许多事一下子明白了:这本书不是一般书,不是白纸黑字,师父也绝不是肉体凡胎……真是相见恨晚!随着学法炼功和心性的提高,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很快除掉热水袋,脱了棉帽、棉鞋……三个月以后,我走出家门。
已记不清多久没出过房门,皮肤已成了没见过阳光的苍白,脚、趾、踝大小关节都疼,我走了很久才到炼功点,就是这天凌晨,一股热流从头灌到脚,通透全身,连指、趾都通透,从法中我知道这是师父为我灌顶。师父啊!我用什么报答您!在炼功场当炼第二套功法时,正抱轮,一个粉红色的法轮、金光闪闪由远而近旋转而来,直到太极图清晰可见。那个颜色漂亮之极,人间没有……说来神奇,炼完功回来,趾、踝关节一点也不疼了,步态如常,身体轻松,很快走到家。
随着心性的提高,我身心健康、愉悦。我三生有幸,得了法了,康复了,先生也得了法了,我们十数年未吃过一粒药,不仅为国家节约了钱财,还能为儿女做一些事。人心向善,必然带来社会安定。
二、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操控权力造谣、诬陷、煽动仇恨,妖魔化法轮功,使我在亲友、朋友、同事、邻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于迫害,一下子成了敌对势力,有的邻居甚至监视、告状、划清界线。昔日的同事相见不相识。亲朋远离而去,过去家人都视我们为骄傲,这回不同了,我的妹妹是市妇联主任,到她家未坐片刻就被骂开了,叫我带上行李走。小表弟的女儿,正上初中,一听法轮功,就讲:法轮功为了圆满会杀人。这是江泽民集团散布的谎言。
但对我的康复都佩服大法,知道大法好。因为我是个,“绝处逢生”的人,姊妹对我的“忍”、对我能坦然面对,那真真是从心中刮目相看了,但谁都怕株连。
三、迫害下我所经受的迫害:
1、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这段时间,第一军医大保卫处长不分时间的来骚扰,开着警车,有时鸣着警笛,车上放着手铐,刘处长对我说:“你知道共产党的厉害吗?你在矮檐下,你敢不低头,我把你送去学习班,文革你经过吗?你知道学习班多厉害。我是处长,我有抓人权!”(注:他把法轮功学员林国雄殴打,并戴上手铐抓到了精神病院,把法轮功学员周士杰抓起来关入小屋……)
一医大附属珠江医院是我先生退休前供职的地方,大家都很熟悉也很了解我们,那时院政委,政治部主任,保卫干事,协理员,科室主任,常常来,还有过一日三次,总是好言相劝,我感到他们的困惑和无奈。
2、二零零零年六月十八日,我们在广州人民公园炼功,被天河区公安分局绑架,在一个小学(名字不详)内关了一日,喷气式,抓头发,强迫照像,饿了一天。在小学被关时的推拉压挤中我右胸二、三肋处受了内伤,剧痛向肩、背四周放射,当晚关在荔湾区一个派出所,晚上在拘留所过夜,疼痛加重,睡觉都困难,前后共关了七天,一位老警(广州人)不时叫骂,并把我坐的凳子抽走,把我摔在地上。两名中年警察不时骂我师父,我抗议他们,他们把我师父的照片取出来,百般的侮辱,一名警察以让我可以洗澡为名,用我的钱给他买了毛巾和肥皂,刑警队长把我在地上拖拉,我的右膝部擦破了一块皮。
绝食五日放我回家,警察跟踪到家,次日与居住地白云区同和派出所警察上门。我讲了我的情况,最后,警察歉意握手,讲:执行任务!执行任务。
3、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广州火车东站被车站警察绑架,抢走了价值三百多元的广州——北京的火车票,用对讲机敲打头部。在车站派出所搜身,翻包,一天未给饭吃,晚上送至广州市收容所。
4、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广州东站警察用警车把我送到广州收容站,这个收容站,工作人员穿黄色警服,无警号,据说不属于警察编制,但有手铐,电棍等械具。
这个收容站是打死大学生孙志刚的地方,我就在此时关在此地,工作人员有一口头语:“法?什么是法?在这儿我就是法!”。
(一)非法囚禁:法轮功三十五人,关三房,我们房五㎡左右,关十三人,是过去关精神病人的地方。铁门、铁窗加锁,从来不放风,室内一点五平方米左右一张水泥床,一个旱厕三层楼上下相通。我们随身携带的衣物全部收走,大冬天全部只能穿毛衣。十三个人只有五床被子,两床棉毯。就是这样,冬天夜间风呼啸着警察用一桶冷水泼我们,几次还喷辣椒水。对我们从来不供洗漱水,脸也很少洗,不洗澡,不换衣服。
(二)每人每天收取六元生活费,一日两餐,全部霉米,米饭每餐不足二两,元旦过后每餐仅供鸡蛋大一块饭,有时把米在开水内焯一下,就吃生米。菜是白水煮白菜、煮萝卜,没有油。不知有多久给一个鸡腿叫加餐,但法轮功学员不供给。饭后可供少量的饮用水,这儿有一句话:“我管不下你们(指不放弃修炼)我要把你们冻的,饿的趴下。
(三)敲诈钱财:一支圆珠笔芯五元,打一分钟电话五元。警察每周会餐一次,把吃剩的菜,鸡头、鸡脖、骨头之类加在关押者的饭上,形成满满一碗,每碗十元(二零零一年时的物价)高兴的时候,还会卖给法轮功学员。发霉的厕纸市价不过几毛钱,这儿两元一卷,方便面市价五~六毛钱一包,这儿卖一~二元,售物从不找零,钱一到手就没有任何收回的余地。要不要由不了你,隔窗扔进去完事……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日,警察用电棍电击从广州火车站截回来的两位欲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我们在二楼看得清楚:电棍冒着兰光,电的学员满院子乱跑,又吼又叫,十分恐怖。元旦那天,把我们都集合到一楼,拉出来一个收容来的湖南女青年,电击、背铐,再电击,给我们看。然后用电棍指着一个青年的法轮功学员出列,一个女警手持电棍指指点点、喊喊叫叫准备电击,杀鸡给猴看。我们迅速的把学员包围住。警察怒了,叫来许多男警,多方准备后,用电棍指着电击过的那个女青年,强迫她在黑板上抄写诽谤法轮功的文章。两个男警左右各一,分别拉我们上二楼。拉的过程多是“喷气式”。我被两名男警拉在一、二楼之间过渡段及房门口时,两人同时做了一个相同的很协调的动作:他们稍事休息,然后两人同时拉着我,同时脱手,猛力向前推。这一推,人会趴在地上,头正好会碰在台阶沿上、床沿上,会碰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甚至颅脑损伤。我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两次都是不自觉地迅速的一百八十度旋转,分别坐在楼梯上、床沿上。没受任何伤。我知道这正是师父在呵护我。
不记得哪天警察把我们搜身赶出来把房子翻了又翻,然后又赶回去,夜间和精神病人关在一起。
5、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日前后(具体时间记不清)海珠区南石头派出所警察肖某和两名年轻警员从收容站把我接走,出站那天强迫填什么表(未叫我看)叫我签字,我不签,几个警察拉的拉,推的推,一个女警在我的腋窝抓痒痒,肖某强行拉开我的右拳,在一个什么表上(未叫我看)和一张白纸上强行按下了五个手指头的印模。
这一天,我被拉到南石头派出所,肖某高兴的大叫,我可以吃鲍鱼餐了,但他没有叫我吃任何东西。晚上,两位年轻的警员说送我去区政府和领导谈话,当我一下警车还没弄清咋回事,他们塞给我一张“拘留证”,铁门开了,我被推进去,他们象逃跑似的跑掉了。
6、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日至二零零一年四月四日在南州路海珠区拘留所我被关了十五天,这儿骗走了我七十八元。拘留所里落地一张木板床,铁门、铁窗,犹如监狱,这儿蚊子大得出奇,密度极大,根本无法入睡。但这里的警察没有刁难过我。
7、二零零一年四月四日至二零零一年四月十月我被关在海珠区东方旅社,由南石头各居委治保主任看管,有关方面帮我买了生活用品,饭菜供应也很好,但没有人身自由。
8、二零零零年四月十日,我被警车拉到广州大道南何贵荣夫人福利院八楼关押,这儿挂:“海珠区法制教育学校”的牌子,其实是臭名昭著的洗脑班。工作人员由公、检、法、司、民政、教育、妇联、共青团组成,由海珠区公安分局某科科长负责。
电梯上八楼就装有不锈钢门,由一保安把守、自称是密闭的半军事化管理。墙上挂满了谤师、谤法的文字和标语、漫画,基本上是一个学员一室(转化的除外),门镜反装,我的房内同时关过一个精神病人,洗脑班造谣说:炼法轮功走火入魔了,还准备制成录像欺骗他人。后来在学员共同强烈抵制下,没有得逞。在这儿,一个学员两个包夹二十四小时轮班看守,每班还得有口头的和文字的交接,一言一行记录在案(第一道岗)。学员不许出房门,隔室对视都不行,绝对不许学法炼功、交谈。阳台上房与房之间都由不锈钢板相隔。走廊两端各坐两人,二十四小时轮班看守(第二道岗)三位保安二十四小时三班轮回在走廊巡逻,也入室巡查(第三道岗)。三位民警,轮流值班巡视。(第四道岗)最后工作人员按学员分工包干。(第五道岗)。学员的吃、喝、着衣、行动、探视均由洗脑班负责人一人掌控。四月十日“开班”那几天、广州大风气温急骤下降(大约四~六度),大家都穿上了棉衣,有的还穿了皮衣,可是因为我要求家人送衣服必须会见,所以就不许家人送衣服,我仅仅穿了一件T恤,上着一件两层的马夹(背心),下穿一条夏季穿的薄单裤。洗脑班企图用“冻”给我一个下马威。
因为我不转化,我的饭菜总是比别人差,洗脑班不让我吃早餐,我吃不了的饭菜想放次日当早餐,洗脑班不许我放冰箱。
开班十天左右,法轮功学员刘少波被迫害致死。
这儿主要是谈话,不许看规定以外的任何东西,悲哀的是报纸、杂志、甚至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不能看。找一些科痞、编一些歪理邪说洗脑,找邪悟的骗导,到各劳教所交换学员、洗脑交流。写什么三书、五书、骂一骂师父和大法、吃点药、喝点酒表示不炼了,甚至歌颂一下谁,达到洗脑状态,视为合格、验收出班。
我拒绝转化,绝食抗议迫害,绝食八天,于二零零一年九月下旬(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家人把我接回家。
9、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三日,快过中秋,儿子、儿媳都在受迫害,我去亲家看望两岁半的小孙子,一场大雨过后,有色金属研究院伙同天河派出所的警察来了四、五人,以我同是炼功人的名义绑架,我被抬上警车至天河街派出所,又转到南石头派出所,当晚,我再次被关入该洗脑班。
10、时隔一年,洗脑班给我的感觉邪恶了许多,除了管理上的更严厉外,每房增加了一台电视机,不断的播放那些造谣的诬蔑大法与师父的录像,还多了一个高分贝的喇叭吵闹不休。九楼增设了一个从劳教所取经验回来的酷刑屋。在这儿不转化的学员弄到酷刑屋迫害,甚至把探视的家属(炼功人)乘机关入迫害。九楼的酷刑屋关过王青梅、沈元惠等人,酷刑屋不仅太阳直晒、暴晒,高音喇叭,刺耳的尖叫。从劳教所才学来的把人绑成球形的残忍,致使几位学员内伤很重,更可恶的是:屋内有厕所,厕坑及地上都有师父的像片或名字,学员根本没有地方站立、坐,如厕,在铁门上靠一靠,警察还用水泼……二零零三年八月一日,这儿变成厨房,洗脑班毁赃灭迹了。
这个洗脑班曾给中山大学硕士画家林娟强制堕胎,不让回家。
为了让工作人员明白真相,使自己生命有个未来,有个良好的归宿。我写了揭批报纸、电视谎言的文章,这下捅了马蜂窝。那时正值非典流行,流行期间,亲民的温家宝总是在第一线,号召全国人民:“国难当头,同舟共济,”我本来是个热心肠的人,救人的使命始终在心,我捐了一百元写了倡议书,倡议学员们赞助钱抗非典,从专业角度写了一份建议,并要求当义工,洗脑班反而加重了对我的迫害,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并(由清洁工)放出话来“想当义工,得脱离法轮功。”还说“非典要的是博士,你又不是博士,政府不批。”这简直奇谈怪论。我在绝食抗议中,洗脑班耍尽了花招。
绝食一周以后,洗脑班不仅不让我出班当义工,开始隔日一次的摧残性强行灌食,灌食在解放军四二一医院进行,每次六克左右米粉,加水约二百五十~三百毫升,内加一个鸡蛋,一点奶粉、每次输液二百五十至五百毫升。先插一个鼻管,用开口器撬开口,再从口内插一个胃管。有一次,把开口器撬开口,长达几个小时,还有几次一面灌食,(这已经够难受的了),这边几个人,拉着一条胳膊抽血说是化验。抽血时往往全身发麻。
这里得提一下海珠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范某,范某自称是区政协主席的儿子,母亲为某医院内科主任。他对借调到洗脑班很有优越感,他很自豪自己是610的人,不存在单位下岗。不可思议他好象从来不懂得“医德”二字。因为我被灌食,他是医生总是“陪医”但他一直在骂我,那张嘴好象从来都没有闲着过的时候,他说:“你不吃饭,我把你弄到医院去喂,喂个狗。喂饱了还知道摇尾巴,我把你喂饱了还不摇。来,摇个尾巴我看看……”煽动的看大门的也跟着骂。他对四二一医院的护士造谣说:我家里没人要我,我儿子都不和我说话。他叫护士用开口器不需要缠纱布,胃管越粗越好。灌食同时抽血的主意来自于范某,他直接动手拉、按、压我的胳膊。他不许我用自己的卫生纸,让呕吐物等直接污秽衣服,在救护车上我一口极度粘稠的痰,无处可吐,只能粘在手上,不许用我自己的卫生纸。去卫生间不许穿鞋,强迫我打赤脚,保安二林用指关节敲打我的额头,他看到很快乐。二零零三年九月七日灌食后,回到福利院,因院内停电,只能走楼梯,范某和保安把我脚朝上,头朝下倒过来往楼上抬,拉扯的衣裤不整,几乎赤身。随身护士一再喊:“有危险”,他根本不理会。我大喊,他才停了下来。我要求自己慢慢走,范某让我赤脚,不许穿鞋,他不停的叨叨、不停的骂。
经过整整八十天的折磨。灌食四十~五十次,我已骨瘦如柴。清洁工把我的头发剪的乱七八糟,炼功后本来黑了的头发又变白,头顶几乎成了秃顶,舌头外沿多处溃疡,下颌、颈淋巴结肿大,大便失禁,膝踝水肿,多次出现晕厥。夹控还要求我坐起。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日,我被家人接回来,当时已无法行走,由救护车送至楼下,保安背我上楼,回来后上述症状加重,腹胀,大小便不能排出。回家后加紧学法炼功,仅仅几周康复。我从内心感激我的师父,又一次给予我生命。
依照刑法,这个洗脑班犯下了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他人,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罪、第二百四十五条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罪,住宅或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滥用职权罪,二百四十六条以暴力或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及诽谤他人罪,二百五十一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二百六十条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罪。
11、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六日,中秋节前一天,海珠区公安分局“610”带领南石头派出所来我家抄家,翻箱倒柜,以抄《九评》为借口,《九评》没找到,就抢劫了我所有的大法书。还企图绑架我,在干休所老干部们抗议及家人强烈的抵制下破产!这些人犯下了《刑法》二百四十五条,非法私入民宅罪、抢劫罪。和二百五十一条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
12、每当所谓的“敏感日”,海珠区的“610”都会多次骚扰,给我的生活带来麻烦。老干部们多有反感,对参与人员的不法行为曾善意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