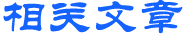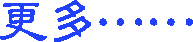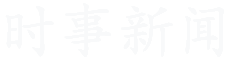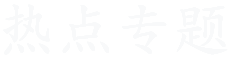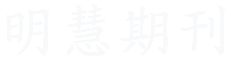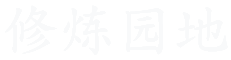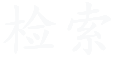“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 一位山东农妇的护法经历
可万万没想到,1999年4月,发生了天津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的事件。我当时想,师父教我们做好人,为无数人祛病健身,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还被诬陷,怎么还被警察抓呢?我和丈夫商量,要去北京,为师父说句公道话。4月25那天,我俩乘车去北京,走到济南时,听功友说中央已经给我们答复了,被抓的人已经放了,我们就回来了。
1999年6月,听说江泽民要陷害法轮功。我想:当权的说了话怎么能不算话呢?这不是瞎胡来吗?!我与丈夫决定亲自到北京找中央政府,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这时,全市戒严,各车站、沿路上到处都是警察,我们看乘车是去不了北京了。我俩就决定骑自行车去,于是,我俩骑上车就上了路。离家不远天就开始下雨了,越下越大。我心里想,就是下刀子,也挡不住我到北京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我要问问他们:为什么能救人命、教人做好人的好功法不让炼,到底安的什么心?沿途有许多岗卡检查盘问,我们就绕路走。有时一天顾不上吃饭,也不觉饿。骑车时间长了,臀部都磨破了,出了不少血,疼得不敢碰车座,但是我俩仍然坚持着,……四天后我俩到了北京。还未到信访办,就被警察截住了,问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回答来上访,为我们师父、为法轮功讨公道来了。警察一面假惺惺地说给我们向上反映意见,一面却把我们关起来了。当时那里面已关了20多个功友,大家都向警察洪法。到了下午,我们镇(潍城区于河镇)去车连夜把我夫妻俩人拉了回来,关在西关派出所,第二天上午8点左右,镇上的谭春起就去了,一见面他就破口大骂,我就给他讲道理,他也不听,给我们村支书打电话,说拿4000元钱来领人。村支书说没那么多钱,只拿来2000元,把我们接回家去了。回家后,我想自己做得对,凭什么罚我们钱。我就给市政府等部门写信上告,先后寄出去11封上诉信。
回去后镇政府的郭新月到我们村说给我们办什么“学习班”,一天不去一天就罚50元钱,还说,不写“保证书”,不交出大法书,就得天天去,不让干自家的活,直到“草鸡”(方言,屈服的意思)为止。我说,到什么时候我也炼,因为我的病是师父给我治好了,我这是第二条命。最后镇政府一看没了办法,就放了我们。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等坏人对法轮功的迫害进一步恶化,我们夫妻俩又决定去北京上访。在济南转车检票时我被查住了,警察把我关在一个学校里,那里已关了几百名功友。警察逼我们看诬陷我们师父的电视录像。第3天,警察们把我送到昌乐县,不多时我们镇派出所去警察带我。一路上我给他们讲,我从前是一个快病死的人,是我师父给了我这条命,我的良心叫我必须向政府讲真话,告诉他们打压法轮功是做错了,为我师父讨回公道。警察说,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可是“政府”就是不让炼,我们也很为难。刚到镇政府,镇上的电工陈龙山就把我从车上拖下来,连踢带打的把我打倒在草坪上,镇政法委书记王新民说::“你还挺厉害,还上政府告我们,我看看你厉害还是我厉害。”说完恶狠狠照我头部猛打一掌,我顿时觉得天昏地暗,转了两圈才站稳,他紧接又狠打一掌,把我打的又反方向转了两圈。暴徒们疯了似的边打边骂,从下午6点一直打到晚上10点多,我前胸、胳膀全部被打成黑紫色,头发散乱着……第二天,暴徒们除了打我之外,逼我坐在水泥地上,伸直双腿,平举着双臂,还在臂上给我挂上提兜。晚上,毫无人性的恶徒们逼我站在院子里的草坪上说是喂蚊子。……歹徒们一连四天四夜这样折磨我,不让我睡觉,逼我写“保证书”,说不写就罚5000元钱。就这样迫害了我12天,最后逼我亲戚交了700元钱才放了我。
回家后我在床上躺了1个多月,胸部疼得不敢喘气,起身坐卧都是我丈夫、儿子扶着我。我刚好了没几天,镇上又逼我们去参加什么“学习班”,暴徒们大会小会点我夫妻俩的名,王新民威胁我们说:“谁要是再上北京,看我怎么收拾你,把你的胳膊腿挑零散了,我不信治不了你。”强迫我们每天两次到村办公室“汇报”,逼我们交了1200元所谓的“保证金”。恶人们还经常半夜三更到我家砸门看看我们在不在家,或爬到我家平房顶上监视我们,弄的街坊四邻都不得安宁。
1999年12月20日,我和一位同修又去北京上访,在车站检票时被恶人发现,镇派出所把我们带回去,用手铐把我们吊在院子里的树上,只让脚尖刚刚触地,还把我俩的棉衣强行脱去,冻我们。从凌晨2点一直铐到第二天9点,两只手都成了黑紫色,它们才把我俩放下来,紧接着就打我们。打我的人叫藏威,它边打边问:“是谁叫你去的北京?只要说出是谁叫你去的我就放了你。”用手打了我七十多下,把我打得满脸是血,嘴唇肿得很高,也成了黑紫色。见我们什么都不说,又把我俩送到镇司法所。王新民、陈龙山等几个恶人,在那里又开始用刑,手脚、棍子、电警棍一起用。王新民残忍地狠踢我丈夫的肋骨,疼得他不敢吸气,将他的后背、臀部打成了青紫色,前胸也肿得很高,一片片的青紫。暴徒们边打边叫喊着:“你俩不是好上北京吗?不怕挨打你们就去。”见我们不屈服,就又逼着交2000元才能放我们回家。亲戚们为了救我俩,就又凑了2000元钱交给镇上,恶人们这才放了我们。回家后我俩都躺在床上不能动,生活不能自理,一个月中都是不到20岁的儿子,帮着我俩穿衣服、服侍我俩。
2000年4月12日,我和几个功友商定再去北京上访。因我们几家都叫镇政府恶徒们非法勒索得几乎倾家荡产,甚至欠债累累,没有去北京的车费,我们便决定步行去。为了不让恶警发现,途中我们都是绕路走。有时1-2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渴极了就找沟里的脏水喝一点。脚底磨的泡连泡,脚趾头上都有大血泡。累的坐下起不来,起来不敢坐,累极了就找个草堆躺一躺,有时浑身难受也睡不着。有时走1-2百里路没有村庄,我们就在路沟里歇息。途经无棣县时,正遇上筑路,一路全是沙堆、石子堆、土堆,没有平路。我们互相鼓励,背诵师父的《洪吟·登泰山》,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不但不觉累,心里还很愉快。有一天,走累了,碰到路旁有一堆麦草,原以为这会儿能睡个好觉,谁知正睡得香时却下起了大雨,我们被淋醒爬了起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笑了。浑身沾满了草,都成了“草人”了。还有一次,我们用玉米秸扎了个小棚子在里面休息,正睡着来了暴风雨,小棚被吹散了,我们就跑着笑着去追捡被风刮跑的玉米秸,真与师父说的一样,“吃苦当成乐”(《洪吟·苦其心志》)了……在路上我们遇上三次沙尘暴,吹得我们站都站不住,我们就从沟里走,我心里想,就是爬我也要爬到北京。我们走累了休息时就学《转法轮》,到北京1200多里地走了12天,正好学了一遍《转法轮》。当我们到了天津市武清县时,警察发现了我们是大法学员要上访,便非法拘留了我们半个月。在拘留所里,当警察审问时,我们堂堂正正地向他们洪法,并讲了我们在途中的经历,有的警察也被感动了,一个警察说:“我相信你们有那么大的毅力,能赤脚到北京,很快会给你们平反的。”并主动给我们提供被子,搜身时,摸到了《转法轮》也没吭声。我们天天坚持学法炼功。
5月14日,我们镇上去车拉我们。去了3个人,其中两个打手气得眼都发了红、露着凶光。他们拉着我们还没出天津市,就迫不及待地停下车,疯狂地打我们。一个姓王的把我拖下车,铐在树上打,边打边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他就更是发了疯似地没头没脸的打,打得我鼻口出血,衣服都染红了。他对我又威胁又利诱,说:“你要炼就送到司法所,你又知道司法所那个厉害。说不练就送你回家,你一次次去北京图什么,在家炼谁管呀。你不想给儿子找媳妇吗?”我说:“俺也不愿意这样,都知道去一次北京被抓住就要扒一层皮,还要罚钱,谁愿意啊?可是这全是政府造成的,不是俺的错。俺老师教俺做个好人,事事为别人着想,做个更好的人,根本就没有错。”他被我说的没理了。这时来往行人都在看他们打人,他们心虚,就把我们解开铐子拖上车。下午6点钟一到我们镇上,就把我拖下车来,10多个人扒去我的外衣,把我按在地上,有的踩脖子,有的踩腿,用电警棍、皮管子、木棍、四棱粗木条等围着打遍我的全身上下。王新民还把我内衣掀起来用胶皮管猛抽我的后背,打得皮肤都成了黑紫色,肿的很高,起了许多血疱。一直打到12点时,我昏死了过去,……他们怕我死了,两人一班轮流看管我。我在昏迷中听到它们谈论,说如发现她不行就快送医院,还说有许多功友曾在我家交流过,要向我问清楚后抓人。我当时想:想让我干出卖功友的事,就是你们把我打死,我也不会干那个事。
第二天一早,滁云生(2000年任镇政法委书记)带领七、八个人继续拷打我,逼我说出到过我家的那些功友的姓名、住址,我说“不知道。”陈龙山从火炉上提起一壶滚开的热水悬在我头上,问我说不说。我仍说不知道。它们一看用刑是“没治”(方言,没办法)了,就又威胁我,说要封我家门,没收我家的机动三轮车,卖我家的房子,我都不动心。他们不死心,就天天折磨我,6天打了我9次,每次都是把我打得不能动了才住手。打得我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地方,全身黑紫,一动就疼,臀部起了个大脓血疱,流着血水。我面黄肌瘦,大小便都不能自理,需要别人帮扶,我整个人被折磨得都变了形,没人模样了。后来,恶徒们怕出人命,只好把我送回家。由于恶徒们经常三更半夜去抓我丈夫,抓不到,又想抓我儿子做人质,所以我丈夫、儿子都躲了出去,有两个月没回家了。我躺在床上动不了,都是我那70多岁、身有残疾的婆婆住在我家照顾我。邻居去看我,见我被打成这样,都流着泪说:“打你的这些人真是畜生,心狠手毒、太缺德了。”我就借这个机会洪法,给他们讲真相。邻居们称赞我真坚强,说炼法轮功的要都这个样,就一定能很快平反。
回家第五天,滁云生、陈永华又到了大队书记家,逼我去“学习”。书记说:“她还呆在床上不会动弹,吃喝拉尿都是70多岁的老人(婆婆)照顾,你让她怎么去。”后来滁云生又商量找人把我叫到支书家,来家看我的两个邻居把我扶到支书家,邪恶之徒一看见我就说:你想办法把你丈夫(大法弟子张志友,现已被邪恶之徒迫害致死)找来,要不的话,和你没完,找到他再拿上3000元钱就完事。后来又来家找我丈夫,我婆婆哭着说:“赶快找亲戚凑钱把他找回来吧,要不怎么办,眼看就要割麦子了,你又不能动,这活怎么干?”好不容易凑了2700元钱,叫着大队书记一起去了镇上,书记刚一走,滁云生和陈永华就没头没脸的打起我丈夫来,用电棍子电、胶皮棍打、皮鞋踢,打的我丈夫满身红紫,脚肿的不敢走,还逼他去锄草,到了晚上又打他,问我丈夫:你老婆去北京你知不知道?潍坊炼功的去你家有几个人?我丈夫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就这样什么也没问出来。
在这期间,我与我丈夫通过学师父的经文《走向圆满》,发现了自己的执著与不足,认识到自己就是师父讲的“有人觉得大法能治好自己的病”的那种人。以前的上访主要是出于我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没有在法上认识法。找到了自己的不足,认识到无论怎样也不能配合邪恶的指使,于是我们夫妇于2000年10月4日再一次进京上访。坐车时遇到岗卡检查也不问我们,一路顺利到了北京。可一进天安门广场就被便衣发现,把我们带到潍坊驻京办事处。恶警们把我们几十人从北京拉回潍坊,路上,我丈夫因为不配合邪恶,被迫害致死。我当时不知道,在被非法关押七天后,镇上才告诉我,让我到沧州去处理后事。走之前,滁云生威胁我,要我“老实”点,不许“乱说”,并无人性地说:“你别以为你丈夫死了,就没有你的事了。还得判你三年劳改。”而我提出的条件它们一个也没有答复。从沧州回来的第三天晚上,邪恶之徒不顾我刚刚失去丈夫的痛苦,又把我抓去非法关押了一个月。镇派出所对我非法审讯时,那所长拿出判我劳教的材料让我看,问我:“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我说:“法正过来就是个头。”一个月后,它们只好放我回家。回家后第3天晚上,村治保主任又通知我:明天镇政府来人“接”我去办“学习班”,我立即悟到坚决不能配合邪恶,不能让其阴谋得逞。我对儿子说:“这个家我不能呆了,我得走。”我就离家出走了。我刚走,镇上就去人抓我,扑了空。
此后,镇上的恶徒们经常去我家骚扰,还装出伪善的面孔欺骗我儿子,要我儿子把我找回来。我儿子生日的那一天,我也流离失所好长一段时间了,就回了趟家想看一看儿子。谁知刚到家,镇政府的陈永华就带领四个打手闯进了我家院子大门,我便闪进了里屋发正念:不许他们到这里屋来。他们在外屋问了我儿子一通,我儿子没配合他们,他们就走了。我又不得不离开了家。
2001年2月份,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养活二老,我在流离失所中找了一个临时工作。3月2日我正在工作单位的楼上干活,镇政府的陈永华带领四个人闯进单位去抓我,一个同事急忙通知我,并把我藏在阳台上,还把我视为命根子的三本大法书也藏好了,又用被子把我盖起来。门还没关上,恶人们就闯了进来,楼上楼下的翻了个遍,没找到我他们就出去了。我认为他们走了,就准备下楼,一开门,看见陈永华正上楼,与他照个面对面。我立即把门关上,我用整个身体顶着门,他在外面连踢带推,累的喘粗气,眼见进不来,他就说好话骗我开门,我坚决不开门,他没有办法了,就只好走了。趁这个机会,同事又把我藏在了一个有痴呆症的老人的铁箱子里,锁上锁,那些恶徒们去搜了几次也没搜到。但是因为那铁箱子不透气,我差一点憋死。傍晚7点钟,好心人用车把我送了出来,并鼓励我要坚持下去。发了疯的恶徒们那一天就去了那单位9次,到夜间12点钟时又去了两辆车,带去许多人,提着手铐进去搜。同事们问他们:“你们说得好听,不抓人还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我们做了多年生意,第一次遇上象李姐(指我)这样的好人,工作实在,有条有理,我们把下面的工作都交给她管。你们把她丈夫害死了,连个寡妇老婆你们都不放过。” 恶徒们狡辩说:“你们不了解情况。”同事说:“怎么不了解,李姐身上还有你们打的疤痕,还有大硬块,有事实证明,你们再说也没用,俺也不信你们。”说的他们没有理了,找不到我,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因为修炼法轮大法,使我这个快死的人绝处逢生,也因为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说假话,不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实事求是地向政府反映情况,而被江罗犯罪集团迫害得家破人亡,至今我还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我那孤苦伶仃的儿子也整天提心吊胆地生活着。我原本好端端的一个家,就这样叫这些恶人给毁了。
两年来的流离失所,日子是苦的,这完全是邪恶迫害造成的,我是坚决否认的。我现在在正法的洪流中,尽力地做着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事情,我又真的觉着自己是那么荣幸……
(英文版:https://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18/23244.html)
(英文版:https://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19/23275.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19/23275.html